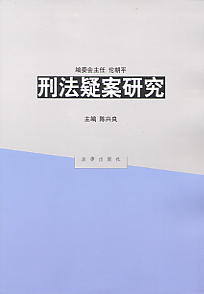
《刑法疑案研究》
8.李恭元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案——犯罪預(yù)備與犯罪未遂的區(qū)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恭元,男,30歲,浙江臨海市人。
2000年3月,被告人李恭元先后從他人手中購(gòu)得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及非法制造的發(fā)票伺機(jī)出售牟利,后經(jīng)群眾舉報(bào)被抓獲。警察同時(shí)在其暫住處起獲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34本,共計(jì)850份,非法制造的發(fā)票5458本,共計(jì)136450份。
我院認(rèn)定李恭元的行為構(gòu)成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犯罪預(yù)備)、出售非法制造的發(fā)票罪(犯罪預(yù)備),將此案訴至海淀法院。海淀法院認(rèn)為,被告人李恭元已將涉案發(fā)票藏匿于住處伺機(jī)出售,因被民警查獲,其行為應(yīng)認(rèn)定已著手實(shí)施犯罪,故應(yīng)認(rèn)定系犯罪未遂。被告人李恭元所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涉案發(fā)票850份,數(shù)量巨大;所犯出售非法制造的發(fā)票罪涉案發(fā)票13萬余份,情節(jié)嚴(yán)重;鑒于其行為系犯罪未遂,依法對(duì)其所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減輕處罰,對(duì)其所犯出售非法制造的發(fā)票罪從輕處罰。據(jù)此,判決如下:被告人李恭元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判處有期徒刑9年,罰金4萬元;犯出售非法制造的發(fā)票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罰金5萬元,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10年6個(gè)月,罰金9萬元。
我院認(rèn)為海淀法院的判決確有錯(cuò)誤:1.被告人李恭元的行為應(yīng)為犯罪預(yù)備,而非犯罪未遂。2.對(duì)其所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的罰金刑適用有誤,應(yīng)在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幅度內(nèi)決定罰金的具體數(shù)額。而判決卻在該幅度以下判處罰金,顯系不當(dāng)。據(jù)此,依法提起抗訴。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支持了我院的第二點(diǎn)抗訴意見,沒有支持第一點(diǎn)抗訴意見。
被告人李恭元以一審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其辯護(hù)律師的辯護(hù)意見是,李恭元的行為應(yīng)屬犯罪預(yù)備,而非犯罪未遂。
北京市第一中級(jí)人民法院對(duì)本案審理后認(rèn)為,李恭元以牟利為目的,購(gòu)買大量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和非法制造的服務(wù)等行業(yè)發(fā)票欲出售,其已經(jīng)著手實(shí)施犯罪行為,由于公安機(jī)關(guān)將其查獲,才使其犯罪未能得逞,因此,原判對(duì)李恭元定罪準(zhǔn)確,認(rèn)定李恭元的犯罪行為是犯罪未遂正確,對(duì)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的主刑和出售非法制造的發(fā)票罪量刑適當(dāng),應(yīng)予維持。但對(duì)李恭元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判處罰金4萬元;適用法律不當(dāng),依法改判。于 2001年9月6日判決如下:撤銷海淀法院判決;李恭元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判處有期徒刑9年,罰金5萬元,犯出售非法制造的發(fā)票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罰金5萬元,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 10年6個(gè)月,罰金10萬元。
二、爭(zhēng)議問題
1.購(gòu)進(jìn)偽造的發(fā)票尚未出售,是犯罪預(yù)備還是犯罪未遂?
2.對(duì)于數(shù)個(gè)罰金刑,應(yīng)如何并罰?
3.對(duì)罰金刑如何減輕?
三、評(píng)析意見
1.李恭元的行為應(yīng)為犯罪預(yù)備,而非犯罪未遂
出售非法制造的發(fā)票罪、出售偽造的增值稅發(fā)票罪,是司法實(shí)踐中的常見多發(fā)犯罪,在犯罪形態(tài)上均屬行為犯。行為犯的既遂與未遂問題,在理論與實(shí)務(wù)中均存在很大爭(zhēng)議。明確行為犯既遂與未遂的標(biāo)準(zhǔn),不僅有利于檢察機(jī)關(guān)在支持公訴過程中充分行使求刑權(quán),而且也有利于法院對(duì)證據(jù)標(biāo)準(zhǔn)有統(tǒng)一的評(píng)價(jià)依據(jù),作出可能對(duì)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的判決,以維護(hù)被告人的合法權(quán)益,平衡國(guó)家利益與個(gè)人利益的沖突,真正實(shí)現(xiàn)司法公正。因此,如何正確劃分行為犯的既遂與未遂,就成為司法實(shí)踐亟需解決的問題,我們就這一問題談點(diǎn)認(rèn)識(shí)。
在英美法系國(guó)家,受其判例法特色的影響,一般沒有把行為犯作為一種犯罪類型加以研究。但近些年,隨著英美法系國(guó)家制定法的增多,行為犯這一概念才得到普遍關(guān)注,開始有人把依據(jù)危害行為而非危害結(jié)果來下定義的犯罪稱為行為犯。而大陸法系卻是最早把行為犯和結(jié)果犯這兩個(gè)概念作為對(duì)應(yīng)的范疇加以研究。我國(guó)刑法學(xué)界對(duì)行為犯的界定主要有兩大類觀點(diǎn)。一類是既遂標(biāo)準(zhǔn)說,從犯罪既遂的角度解釋行為犯,認(rèn)為只要實(shí)施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危害行為就稱為既遂的犯罪。其中又有幾種不同的觀點(diǎn):(1)行為犯就是形式犯,行為犯既遂又稱形式犯既遂,是指以一定的危害行為完成作為構(gòu)成要件的犯罪既遂。(2)行為犯包括舉動(dòng)犯和過程犯;(3)行為犯不同于舉動(dòng)犯,二者的區(qū)別在于行為犯有既遂和未遂之分,舉動(dòng)犯無既遂和未遂之分。(4)行為犯與舉動(dòng)犯是同一概念,只要有一定的行為即構(gòu)成犯罪的是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單純地實(shí)施了刑法分則所規(guī)定的構(gòu)成要件就足以構(gòu)成犯罪,而無需發(fā)生一定的犯罪結(jié)果。另一類是成立標(biāo)準(zhǔn)說。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從法律規(guī)定的犯罪構(gòu)成或法律條文本身規(guī)定來判斷某一犯罪是否為行為犯。如果條文沒有規(guī)定特定犯罪結(jié)果,只規(guī)定危害行為,那該條文規(guī)定的犯罪就是行為犯。
我們贊成既遂標(biāo)準(zhǔn)說,我國(guó)刑法分則對(duì)法定刑的設(shè)置是以處罰既遂犯為標(biāo)準(zhǔn)的,而且既遂犯是犯罪普遍存在的形態(tài)。立法者在確立法定刑時(shí),更多地考慮了既遂犯罪行為是否會(huì)造成一定的社會(huì)危害性。如果堅(jiān)持刑法罪刑相適應(yīng)的原則,我們不可能想象法律會(huì)把一種犯罪的未遂狀態(tài)作為定罪量刑的標(biāo)準(zhǔn)。因?yàn)橹挥蟹缸锛人觳拍茏畛浞值伢w現(xiàn)犯罪構(gòu)成,當(dāng)然立法者在立法時(shí)必須運(yùn)用簡(jiǎn)潔明了的語(yǔ)言,僅以法律條文對(duì)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表述判斷行為犯或結(jié)果犯太過于表面化。如果僅以條文本身規(guī)定行為犯難免會(huì)造成打擊過嚴(yán),不利于保護(hù)被告人人權(quán),導(dǎo)致司法權(quán)的濫用。由此,我們可以給行為犯下一個(gè)定義:行為犯就是指實(shí)施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而無需發(fā)生特定的危害結(jié)果即可以成立既遂的犯罪形態(tài)。這里特定的危害結(jié)果既包括實(shí)際損害結(jié)果,也包括可能實(shí)現(xiàn)的危害結(jié)果。
由于對(duì)行為犯定義理解的不同,對(duì)其犯罪既遂、未遂狀態(tài)自然也存在分歧。
實(shí)務(wù)中在認(rèn)定行為犯既遂與未遂問題上存在兩方面分歧。一是行為犯是否存在既遂、未遂狀態(tài)。二是如何確定假發(fā)票犯罪行為犯既遂與未遂的標(biāo)準(zhǔn)。有觀點(diǎn)認(rèn)為行為犯無未遂,認(rèn)為行為犯等同于舉動(dòng)犯,即只要一著手實(shí)施犯罪既構(gòu)成既遂。我們認(rèn)為這種觀點(diǎn)是不全面的,行為犯不僅存在著犯罪的預(yù)備、既遂狀態(tài),也存在著犯罪的未遂狀態(tài),既遂犯與未遂犯的區(qū)分,主要在于實(shí)行犯罪過程中是否存在著足以抑制其犯罪意思的意外因素。在以一定時(shí)間間隔才能完成犯罪的情況下,著手后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遂形態(tài)是可能存在的。我們認(rèn)為,故意犯罪行為(包括行為犯的行為)總存在一定的發(fā)展過程和階段,只不過不同的行為過程和階段長(zhǎng)短不一。就行為本身來看,著手實(shí)施犯罪與犯罪實(shí)行完畢等同的觀點(diǎn)是錯(cuò)誤的,行為人在著手實(shí)施犯罪之后,還需將此行為持續(xù)一段時(shí)間,只有當(dāng)實(shí)行行為達(dá)到一定的危害程度時(shí),才標(biāo)志著該行為犯的既遂狀態(tài)。
行為犯總是經(jīng)歷犯罪預(yù)備,著手實(shí)施、實(shí)施完畢這樣一個(gè)連動(dòng)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存在時(shí)間、空間上的間隔與地點(diǎn)的差異。這就要求我們?cè)趯?shí)踐中確定一個(gè)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既遂與未遂的犯罪形態(tài)。我們認(rèn)為對(duì)行為犯犯罪既遂、未遂應(yīng)該確定一個(gè)分界點(diǎn),將行為發(fā)展過程分成三個(gè)時(shí)間段。第一階段為犯罪預(yù)備,表現(xiàn)為行為人為出售假發(fā)票而作準(zhǔn)備,包括去購(gòu)買、偽造發(fā)票等舉動(dòng)。第二階段為犯罪未遂,表現(xiàn)為行為人攜帶假發(fā)票到達(dá)約定地點(diǎn),但由于種種原因(買主未到或警察已設(shè)伏,先將其抓獲)而未將假發(fā)票交給買主。第三階段為犯罪既遂,表現(xiàn)為行為人將假發(fā)票已交付,無論買方是否付款。
就本案來說,被告人李恭元雖從他人手中購(gòu)得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及非法制造的發(fā)票伺機(jī)出售牟利,但其尚未聯(lián)系出售對(duì)象,也沒有條件實(shí)施商談出售數(shù)量,價(jià)格及交付發(fā)票、錢財(cái)?shù)热魏纬鍪坌袨椋湓诩抑胁啬浒l(fā)票是為出售發(fā)票所進(jìn)行的準(zhǔn)備活動(dòng)。因此,其行為應(yīng)屬于犯罪預(yù)備,而非犯罪未遂。
2.對(duì)于數(shù)個(gè)罰金刑并罰時(shí),應(yīng)適用限制加重原則
由于我國(guó)刑法對(duì)數(shù)個(gè)罰金刑的并罰問題未作具體規(guī)定,因此導(dǎo)致理論上的分歧不斷,實(shí)踐中的做法也很不一致。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diǎn):
第一種觀點(diǎn)是吸收說。認(rèn)為在行為人犯數(shù)罪被分別判處罰金刑時(shí),選擇其中最重的罰金刑宣告執(zhí)行,其余較輕的罰金刑不執(zhí)行。我國(guó)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大綱(草案)》也曾采用此種原則。該《草案》第25條規(guī)定:“一人犯數(shù)罪,或一行為而構(gòu)成犯數(shù)罪者,各別宣告其處罰。宣告多數(shù)死刑、徒刑、勞役或罰金者,擇其中最重的執(zhí)行之。”
第二種觀點(diǎn)是并科說。認(rèn)為當(dāng)犯罪分子被判處數(shù)個(gè)罰金刑時(shí),數(shù)個(gè)罰金刑的總額應(yīng)為執(zhí)行罰金的數(shù)額。主要理由是,我國(guó)《刑法》第69條規(guī)定:“如果數(shù)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zhí)行。”這就是說,不管判處多少個(gè)罰金刑,在并罰時(shí)各個(gè)罰金刑都應(yīng)當(dāng)執(zhí)行。如果并罰后罰金刑過高,犯罪分子難以繳納,可以在執(zhí)行過程中給予減免。
第三種觀點(diǎn)是限制加重說。認(rèn)為在所犯數(shù)罪被判處兩個(gè)以上罰金刑的,應(yīng)在其中最重的罰金刑數(shù)額以上,數(shù)個(gè)罰金刑的數(shù)額總和以下決定執(zhí)行的罰金數(shù)額。
我們同意第三種觀點(diǎn)。第一種觀點(diǎn)即吸收說違背了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有失之畸輕之弊。第二種觀點(diǎn)未能正確理解<刑法)第69條的規(guī)定。《刑法》第69條關(guān)于附加刑仍須執(zhí)行的規(guī)定,僅僅指明了主刑和附加刑的并處關(guān)系,即當(dāng)數(shù)罪中被判處主刑和附加刑后,主刑和附加刑都要執(zhí)行,至于所判的數(shù)個(gè)附加刑應(yīng)如何執(zhí)行,第69條并未規(guī)定。那種以《刑法》第69條的規(guī)定作為數(shù)個(gè)附加刑之間應(yīng)采并科原則的法律根據(jù)的觀點(diǎn),實(shí)際上是對(duì)法條的誤解。限制加重說既符合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同時(shí)又考慮了罰金刑與犯罪人支付能力有關(guān)的特殊性,使法院在判處兩個(gè)以上罰金刑后,還進(jìn)一步考慮執(zhí)行的可能性,在最重罰金以上,兩個(gè)罰金之和以下考慮一個(gè)合適的總金額。同時(shí)該說與<刑法)第69條的立法精神也不矛盾。在刑法典起草過程中,限制加重原則曾作為罰金刑并罰的適用原則。195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草案》(第22稿)第68條曾規(guī)定:“判處兩個(gè)以上罰金的,在總和罰金數(shù)額以下多數(shù)罰金中最高數(shù)額以上,決定罰金的數(shù)額。”現(xiàn)行刑法雖刪去了這一規(guī)定,但這種立法精神應(yīng)當(dāng)說并未改變。采取限制加重原則有外國(guó)立法例可供參考。如《日本刑法》第48條第2項(xiàng)規(guī)定:“數(shù)個(gè)以上的罰金,應(yīng)當(dāng)在各罪所定罰金的總和數(shù)額以下判處。”①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們贊同限制加重說,但實(shí)踐中卻必須要采納并科說。因?yàn)樽罡呷嗣穹ㄔ?000年12月13日頒布的《關(guān)于適用財(cái)產(chǎn)刑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采納了該說。《規(guī)定》第3條第2款規(guī)定:“依法對(duì)犯罪分子所犯數(shù)罪分別判處罰金的,應(yīng)當(dāng)實(shí)行數(shù)罪并罰,將所判處的罰金數(shù)額相加,執(zhí)行總和數(shù)額。”《規(guī)定》系有法律約束力的司法解釋,司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遵守。但從應(yīng)然的角度講,限制加重說還是合理的。
3.對(duì)罰金刑的減輕,應(yīng)符合刑法的規(guī)定
在并處罰金刑模式下,主刑和罰金刑組成某一犯罪的法定刑,即刑罰是主刑和罰金刑的總和。主刑刑罰量的變化和罰金刑刑罰量的變化都反映了刑罰的輕重。由此可以推導(dǎo),量刑情節(jié)不僅對(duì)主刑有影響,而且也應(yīng)該對(duì)罰金刑有影響。①具體到減輕情節(jié)來說,如果某罪的法定刑中規(guī)定有罰金刑,行為人實(shí)施本罪后具有減輕處罰情節(jié)并擬減輕處罰,在對(duì)法定刑中的主刑予以減輕的同時(shí),也可以對(duì)應(yīng)判的罰金刑予以適當(dāng)減輕。法院對(duì)本案被告人李恭元所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適用減輕處罰,但對(duì)罰金刑裁量不當(dāng)。根據(jù)《刑法》第206條第1款的規(guī)定,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共有3個(gè)量刑幅度;第一個(gè)幅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第二個(gè)幅度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第三個(gè)幅度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cái)產(chǎn)。對(duì)被告人李恭元本應(yīng)在第三個(gè)幅度量刑,但由于其有減輕處罰情節(jié),因此,對(duì)其減輕處罰,在第二個(gè)幅度內(nèi)量刑。根據(jù)前述分析,對(duì)罰金刑理應(yīng)也予以減輕。但本案有個(gè)例外,就是對(duì)罰金刑實(shí)際上不能減輕。因?yàn)榈诙䝼€(gè)幅度的罰金刑與第三個(gè)幅度的罰金刑都是一樣的,即都是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換言之,既然對(duì)被告人李恭元在第二個(gè)幅度內(nèi)量刑,那就要求不僅主刑在該幅度內(nèi),而且罰金刑也應(yīng)在該幅度內(nèi),也就是說,對(duì)其所處的罰金刑不能少于5萬元。法院對(duì)其判處4萬元罰金,顯然是不妥的。有人指出,本案實(shí)際上僅對(duì)主刑適用了減輕,對(duì)罰金刑并未減輕,不符合刑法原理。我們認(rèn)為,減輕處罰主要是針對(duì)主刑而言的,由于刑法對(duì)兩個(gè)幅度的罰金刑都規(guī)定了一樣的數(shù)額,導(dǎo)致了對(duì)罰金刑不能適用減輕處罰,這是法律的特別規(guī)定。對(duì)主刑的減輕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起到了罪刑相適應(yīng)。所以,我們認(rèn)為法院對(duì)本案的罰金刑適用不當(dāng)。
四、專家點(diǎn)評(píng)
本案盡管涉及三個(gè)問題,但我認(rèn)為最有研究?jī)r(jià)值的還是本案被告人李恭元的行為到底是犯罪預(yù)備還是犯罪未遂。在犯罪預(yù)備的情況下,行為人實(shí)施了犯罪的預(yù)備行為,即為了犯罪,準(zhǔn)備工具,制造條件。而在犯罪未遂的情況下,行為人實(shí)施了犯罪的實(shí)行行為,只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而已。因此,區(qū)分本案被告人李恭元是犯罪預(yù)備還是犯罪未遂,關(guān)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已經(jīng)著手實(shí)行犯罪。本案的犯罪實(shí)行行為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行為,被告人李恭元購(gòu)得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隱藏在家里伺機(jī)出售牟利,其出售行為并未著手實(shí)行,這只是一種犯罪的預(yù)備行為。因此,我認(rèn)為,本案被告人李恭元的行為應(yīng)以犯罪預(yù)備論處而非犯罪未遂。
① 參見周振想著:《刑罰適用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340頁(yè)。
① 參見馬登民、徐安柱著:《財(cái)產(chǎn)刑研究》,中國(guó)檢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y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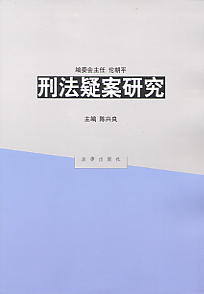 《刑法疑案研究》
《刑法疑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