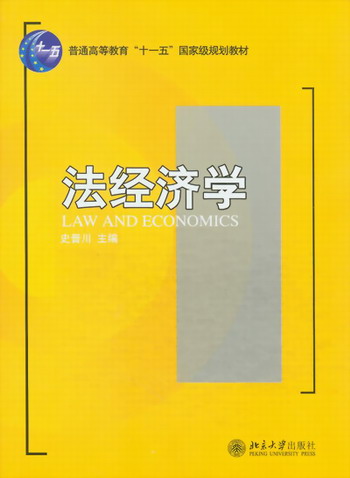
某市“嚴(yán)打”3月重大案破案率100%是功績還是失職?① 據(jù)報載: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個月內(nèi)破獲各類刑事案件l 228起,打掉公安部掛牌的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4個、黑惡犯罪集團21個,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案率100%。讀后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想借貴報問一聲:這到底是功績還是失職? 眾所周知,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和黑惡犯罪集團均非一日可成,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為什么我們的公安部門不能將其控制、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難道該市的這些集團都是在一天或一月內(nèi)形成的?再往下看,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該市公安局實行了民警破案獎懲制,每破一起掛牌案件,市政府獎勵20萬元,對有功民警獎勵2萬元,調(diào)動了民警的工作積極性。同時,對工作失職、打擊不力、出現(xiàn)失誤的民警嚴(yán)肅追究責(zé)任云云,并羅列了一些被處分人員數(shù)字。我不明白:如果沒有上述獎勵,那些犯罪集團和犯罪人員是否仍會逍遙法外?我們的民警就會沒有工作積極性?我不明白,我們的民警拿著國家的俸祿,拿著人民警察的警銜津貼和行業(yè)風(fēng)險金,手握著刑事偵查、治安管理種種特權(quán),并享受著人民警察的美稱,為什么就沒有積極性了呢?在此之前,那些局長、主管領(lǐng)導(dǎo)平日里是否有失職之嫌?為什么能穩(wěn)穩(wěn)地待在領(lǐng)導(dǎo)崗位上? 一個法治的國家絕不應(yīng)是靠嚴(yán)打、專項治理這些運動來保持社會治安穩(wěn)定的,我們應(yīng)著手于日常的治安管理,做好日常的基層工作,做好日常的安全防范工作。如果那樣,我們的社會也將更加安寧。 自從1983年我國第一次開展“嚴(yán)打”行動以來,有關(guān)“嚴(yán)打’’利弊的爭論一直就沒有平息過,上述案例正是這種爭論的一個縮影。理論界對“嚴(yán)打”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即“反對說”和“反思說”,而相關(guān)部門對“嚴(yán)打’’的看法較為一
致,即對“嚴(yán)打”持肯定態(tài)度。①下文將在介紹我國三次“嚴(yán)打”行動的基本概況的基礎(chǔ)上,運用第十三章有關(guān)犯罪經(jīng)濟學(xué)及最佳威懾等方面的理論,從經(jīng)濟學(xué)角度對“嚴(yán)打”作一番理性評價。
我們將從成本一收益、委托一代理兩個角度對“嚴(yán)打”進(jìn)行經(jīng)濟學(xué)分析。 一、“嚴(yán)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從經(jīng)濟學(xué)角度,“嚴(yán)打”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應(yīng)當(dāng)在何種范圍內(nèi)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嚴(yán)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嚴(yán)打”的成本主要包括實際開支成本和其他成本。
(1)“嚴(yán)打”的實際開支成本是指社會為“嚴(yán)打”所支付的、可計算的成本,主要包括了決策成本、偵查成本、訴訟及審判成本、執(zhí)行成本。是否發(fā)動“嚴(yán)打”需要科學(xué)決策,而決策的制定需要搜集一定時期內(nèi)的刑事犯罪數(shù)據(jù)、調(diào)查民眾對社會治安的滿意程度等,這些工作都是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的。我國三次“嚴(yán)打”期初,刑事案件的立案數(shù)都有了明顯的上升,這主要是因為集中了各方面的力量,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結(jié)果。“集中力量”使得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嚴(yán)打”的偵查中,“從重從快”使得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嚴(yán)打”的訴訟及審判中,伴隨定罪數(shù)量增加,監(jiān)獄的執(zhí)行成本也在迅速增加。我國尚未有對“嚴(yán)打”實際支出成本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但參考美國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刑事案件的成本是很高的。④我國關(guān)押一名罪犯,每年就需要花費1萬元以上,一個犯人每年給國家造成的消耗超過3萬元。②一定時期內(nèi),社會的總體資源是有限的,當(dāng)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入到“嚴(yán)打”中時,也就意味著其他方面開支的減少。打擊刑事犯罪、改善社會治安情況是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手段,同時,教育、醫(yī)療、基礎(chǔ)設(shè)施、社會福利等方面也需要社會資源的大量投入。如何合理分配“嚴(yán)打”及其他社會公共開支的比例也是考量“嚴(yán)打”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因為“嚴(yán)打”的過多投入而導(dǎo)致社會總體福利的下降,“嚴(yán)打”將得不償失。
(2)“嚴(yán)打”的其他成本是指除了實際開支成本、機會成本之外的成本,內(nèi)容繁雜、難以計量是該成本的特點。“嚴(yán)打”對法治造成的負(fù)面影響是其中重要的一項成本,也是理論界反對或質(zhì)疑“嚴(yán)打”的重要原因所在。依法治國是黨的十五大確立的治理國家的基本國策,“嚴(yán)打”作為一項刑事政策應(yīng)當(dāng)在社會主義法治軌道上進(jìn)行,“從重從快”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nèi)進(jìn)行。這就要求“嚴(yán)打”不可以突破法律的界限,任意多捕、盲目從重,甚至對犯罪分子隨意加重處罰;也不可以超越法律程序,剝奪犯罪嫌疑人應(yīng)有的訴訟權(quán)利而草率行事、隨意從快。③在實踐中,由于受各種人為因素影響,“嚴(yán)打”往往會在某種程度上脫離法治軌道,從而可能對法治造成某種程度的破壞。這種破壞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過分強調(diào)法律威懾而忽視法律公正,二是過分強調(diào)“嚴(yán)打”業(yè)績而忽視人權(quán)保障,三是過于強調(diào)刑罰強度而可能強化專制。④“嚴(yán)打”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使得民眾對“嚴(yán)打”產(chǎn)生了抵觸情緒。“嚴(yán)打”的收益是指因為“嚴(yán)打”而產(chǎn)生的對社會的正效應(yīng)的增加或負(fù)效應(yīng)的減少。“嚴(yán)打”的收益主要包括減少犯罪、預(yù)防犯罪以及改善民意等。 (1)減少犯罪數(shù)量的收益。“嚴(yán)打”收益最直接的表現(xiàn)在于犯罪率的降低、犯罪數(shù)量的減少。從圖14-2中可知,“嚴(yán)打”在短期內(nèi)確實有效減少了犯罪數(shù)量。1983年第一次“嚴(yán)打”開始后,刑事立案數(shù)從當(dāng)年的610478件下降到1984年的514 369件,在隨后的三年內(nèi)立案數(shù)一直在55萬件左右,立案數(shù)較1983年下降了大約10%;第二次“嚴(yán)打”期間,刑事案件的立案數(shù)從1996年的1 660716件略降到1997年的1 613 629件;2001年開始第三次“嚴(yán)打”后,當(dāng)年的刑事案件立案數(shù)為446.19萬件,2002年較2001年下降了2.8%。刑事案件的下降在“嚴(yán)打”期間十分明顯,但是在長期內(nèi)犯罪數(shù)量又迅速回升并屢創(chuàng)新高。第一次“嚴(yán)打”結(jié)束后的1988年,立案數(shù)回升至827 594件,1989年更是增加到了1 971 901件,較1983年增加了近兩倍;隨著第二次“嚴(yán)打”的結(jié)束后,1999年刑事立案數(shù)突破了200萬件,2000年更是突破了360萬件;第三次“嚴(yán)打”之后,2002年、2003年的刑事案件立案數(shù)均低于2001年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但2004年Y..2z升到了471.8萬件。這表明“嚴(yán)打”無法在長期內(nèi)有效控制犯罪的數(shù)量,我國轉(zhuǎn)型期內(nèi)犯罪數(shù)量劇增有其深刻的內(nèi)在原因,單單依靠外在的“嚴(yán)打”手段是無法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的。 (2)犯罪預(yù)防的收益。犯罪預(yù)防包括一般預(yù)防與特殊預(yù)防,“嚴(yán)打”的特殊預(yù)防是指通過“嚴(yán)打”措施預(yù)防罪犯重新犯罪,一般預(yù)防是指社會一般人群鑒于“嚴(yán)打”的威懾力而放棄犯罪。從定性角度看,我國“嚴(yán)打”期間犯罪率的降低既有打擊犯罪的貢獻(xiàn),也與犯罪預(yù)防息息相關(guān);“嚴(yán)打”通過逮捕更多的罪犯剝奪了這部分人群重新犯罪的機會,而通過監(jiān)獄的改造也可以起到預(yù)防犯罪的功效。社會一般大眾通過各種渠道感知“嚴(yán)打”的威懾力,將有效地阻止其犯罪。“嚴(yán)打”的一般預(yù)防收益較難量化,而特殊預(yù)防收益可以通過重新犯罪率的數(shù)據(jù)來衡量,重新犯罪率越低,“嚴(yán)打”的特殊預(yù)防收益也就越大。我國第一次“嚴(yán)打”期間,成年刑滿釋放人員的重新違法犯罪率為6.59%,同時進(jìn)行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64%的罪犯愿意接受監(jiān)獄的改造,54%的罪犯認(rèn)為自己在刑滿釋放后將不再犯罪,“嚴(yán)打”取得了一定的犯罪預(yù)防的收益。①
(3)改善民意的收益。發(fā)動“嚴(yán)打”的一個重要目標(biāo)是通過打擊嚴(yán)重刑事犯罪,改變民眾對社會治安狀況的不滿情緒。根據(jù)犯罪飽和性生成模型,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社會只能容納一定量的犯罪率,當(dāng)犯罪率超過一定的量時,社會民眾對犯罪的厭惡程度將急劇增加并通過各種渠道向政府施加打擊犯罪的壓力。為了維護統(tǒng)治,謀求公眾福利最大化,政府將采取包括“嚴(yán)打”在內(nèi)的各種手段打擊犯罪,將犯罪率控制在民眾容忍的范圍之內(nèi)。一項調(diào)查顯示,中國民眾對“嚴(yán)打”持“一邊倒”的贊同態(tài)度,90%的被調(diào)查者認(rèn)為“嚴(yán)打”很有必要,86%的被調(diào)查者認(rèn)為在任何時候都要“嚴(yán)打”,44%的被調(diào)查者認(rèn)為當(dāng)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沒有“嚴(yán)打”,63%的被調(diào)查者認(rèn)為“嚴(yán)打”之后犯罪率大大降低。①這一系列數(shù)據(jù)表明,“嚴(yán)打”在改善民意方面的收益是十分明顯的。 在明確了“嚴(yán)打”的成本與收益之后,“嚴(yán)打”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應(yīng)當(dāng)存在的討論就有了經(jīng)濟學(xué)分析的基礎(chǔ)。當(dāng)“嚴(yán)打”的收益超過“嚴(yán)打”的成本時,“嚴(yán)打”就具備了存在的合理性,當(dāng)收益超過成本的幅度越高時,“嚴(yán)打”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也就越大。反之同理。無論“嚴(yán)打”的成本還是收益都是比較難以衡量的,如“嚴(yán)打”對法治的沖擊、“嚴(yán)打”的預(yù)防收益、“嚴(yán)打”對民意的改善都很難從數(shù)量上進(jìn)行比較。因此,在運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來判斷“嚴(yán)打”是否應(yīng)當(dāng)存在以及應(yīng)當(dāng)在多大范圍內(nèi)存在時,就需要仔細(xì)考慮不同社會條件下每項成本及收益的權(quán)重,以便做出正確的決策。
二、“嚴(yán)打”的委托一代理分析以上重點從成本一收益角度分析了是否應(yīng)當(dāng)實施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實施“嚴(yán)打”的宏觀決策問題,“嚴(yán)打”不僅需要科學(xué)的決策,還有賴于良好的實施機制。下文將從委托一代理角度分析“嚴(yán)打”實施過程中的有關(guān)問題。黨中央是“嚴(yán)打”的發(fā)動者及統(tǒng)率者,是經(jīng)濟學(xué)意義上的委托方;各級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門是“嚴(yán)打”的具體實施者,是經(jīng)濟學(xué)意義上的代理方。“嚴(yán)打”實施過程中是否存在委托一代理問題,如果存在,問題有多嚴(yán)重,我們將結(jié)合歷次“嚴(yán)打”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進(jìn)行分析。
1.地方政府及司法機關(guān)追求部門利益現(xiàn)象相當(dāng)嚴(yán)重我們以本節(jié)的開篇案例為例,該報道中的某市公安局竟然在短短3個月時間內(nèi)破獲各類刑事案件1 228起,打掉公安部掛牌的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4個、黑惡犯罪集團21個,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案率100%。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和黑惡犯罪集團均非一日可成,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為什么公安部門不能將其控制、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嚴(yán)打”期間,該市公安局實行了民警破案獎懲制,每破一起掛牌案件,市政府獎勵20萬元,對有功民警獎勵2萬元,調(diào)動了民警的工作積極性。布坎南認(rèn)為,“當(dāng)人由市場中的買者或賣者轉(zhuǎn)變?yōu)檎芜^程中的投票人、納稅人、受益人、政治家或官員時,他們的品性不會發(fā)生變化”②,他們也是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黨中央在進(jìn)行“嚴(yán)打”決策時,其目標(biāo)是嚴(yán)厲打擊嚴(yán)重的刑事犯罪活動,形成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在決策中,黨中央假定作為代理人的各級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門與黨中央有著一致的目標(biāo),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fā)點,能夠盡職盡責(zé)地將黨中央的“嚴(yán)打”決策落到實處。而事實上,一部分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門為了自身利益,追求的并非是黨中央“嚴(yán)打”決策設(shè)定的目標(biāo),而是部門利益的最大化,具體表現(xiàn)為機會主義行動相當(dāng)普遍。在部門利益的驅(qū)動下,在“嚴(yán)打”實施過程中出現(xiàn)下文將要論述的問題,亦是不可避免的。
2.“嚴(yán)打”的“從重從快”與“法治”的沖突相當(dāng)嚴(yán)重作為刑事政策的“嚴(yán)打”應(yīng)當(dāng)遵循“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應(yīng)當(dāng)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彭真同志曾指出,“嚴(yán)打斗爭也是完全在法律范圍內(nèi)進(jìn)行的。”另有同志認(rèn)為,“從重從快是在法律規(guī)定的量刑幅度之內(nèi)從重處罰,是在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之內(nèi)從快處理,而不是盲目從重,更不是重刑思想指導(dǎo)下的多殺、重判,也不是超越法律程序、剝奪被告人應(yīng)有的訴訟權(quán)利,草率從重,隨意從快。”這表明決策者是要依法進(jìn)行“嚴(yán)打”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門為了取得“嚴(yán)打”的政績,采取“限期破案”、“下嚴(yán)打指標(biāo)”等方式,只強調(diào)公檢法三部門配合而不顧權(quán)力之間的相互制約,不遵循刑事偵查、審判的客觀規(guī)律,盲目“從重從快”。某地曾出現(xiàn)一起殺人案件從立案、偵查、起訴到審判總共只花了7天時間的案例,此等案件的質(zhì)量有待商榷。此外,“嚴(yán)打”期間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有違程序正義的現(xiàn)象相當(dāng)普遍。②
3.重打擊,輕日常的治安防范打擊犯罪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不僅需要特殊時期的“嚴(yán)打”,也需要日常的治安防范,將犯罪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但在部分地區(qū)的“嚴(yán)打”實施過程中.往往呈現(xiàn)“重打擊,輕日常治安防范”的不良態(tài)勢。其原因可能在于,“嚴(yán)打”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它所特有的在短期內(nèi)迅速、暫時地遏制犯罪的威懾作用,頗得決策層的青睞,相應(yīng)地,作為回報和激勵,司法機關(guān)能夠獲得較之平時更為豐富的物質(zhì)待遇和更為良好的辦公設(shè)備;而日常的基礎(chǔ)治安工作多是在默默無聞中開展的,所以少有司法機關(guān)或司法人員為其投入充分的人力、物力和精力。③學(xué)者尼斯蘭卡曾精辟地論述到,官員追求的目標(biāo)是在其任期內(nèi)獲得最大化預(yù)算,一個官員可能追求下列目標(biāo):薪金、職務(wù)津貼、公共聲譽、權(quán)力、任免權(quán)、機構(gòu)的產(chǎn)出、容易改變事物、容易管理機構(gòu);除最后兩項外,其余的目標(biāo)都與政府預(yù)算有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①而“嚴(yán)打”可以滿足地方政府與司法部門預(yù)算最大化的需要,決策層在歷次“嚴(yán)打”行動中把給予司法機關(guān)充分的資源配置作為一個重要的配套措施來落實。
如何解決好“嚴(yán)打”中的委托一代理問題,我們可以借鑒經(jīng)濟學(xué)家的經(jīng)典論述。凱威特和麥庫賓斯提出,委托人可以采取四種措施來解決普遍存在的委托一代理問題:一是篩選代理人,通過比較多個代理人后選擇最優(yōu)的代理人;二是合約設(shè)計,合理地設(shè)計機構(gòu)分派管理責(zé)任及規(guī)制方式;三是監(jiān)督和回報;四是制度制約,為政府機構(gòu)設(shè)置一個平衡機制。② “嚴(yán)打”是我國轉(zhuǎn)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特殊產(chǎn)物,本節(jié)的分析并非絕對地肯定或否定“嚴(yán)打”存在的合理性。我們只是從經(jīng)濟學(xué)的角度分析了“嚴(yán)打”的成本一收益問題以及可能存在的委托一代理問題,試圖為“嚴(yán)打”決策提供一個經(jīng)濟學(xué)的分析基礎(chǔ)。
摘自:史晉川著《法經(jīng)濟學(xué)(21世紀(jì)經(jīng)濟管理規(guī)劃教材.經(jīng)濟學(xué)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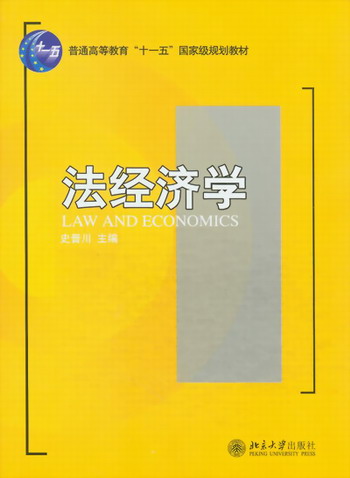 某市“嚴(yán)打”3月重大案破案率100%是功績還是失職?① 據(jù)報載: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個月內(nèi)破獲各類刑事案件l 228起,打掉公安部掛牌的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4個、黑惡犯罪集團21個,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案率100%。讀后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想借貴報問一聲:這到底是功績還是失職? 眾所周知,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和黑惡犯罪集團均非一日可成,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為什么我們的公安部門不能將其控制、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難道該市的這些集團都是在一天或一月內(nèi)形成的?再往下看,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該市公安局實行了民警破案獎懲制,每破一起掛牌案件,市政府獎勵20萬元,對有功民警獎勵2萬元,調(diào)動了民警的工作積極性。同時,對工作失職、打擊不力、出現(xiàn)失誤的民警嚴(yán)肅追究責(zé)任云云,并羅列了一些被處分人員數(shù)字。我不明白:如果沒有上述獎勵,那些犯罪集團和犯罪人員是否仍會逍遙法外?我們的民警就會沒有工作積極性?我不明白,我們的民警拿著國家的俸祿,拿著人民警察的警銜津貼和行業(yè)風(fēng)險金,手握著刑事偵查、治安管理種種特權(quán),并享受著人民警察的美稱,為什么就沒有積極性了呢?在此之前,那些局長、主管領(lǐng)導(dǎo)平日里是否有失職之嫌?為什么能穩(wěn)穩(wěn)地待在領(lǐng)導(dǎo)崗位上? 一個法治的國家絕不應(yīng)是靠嚴(yán)打、專項治理這些運動來保持社會治安穩(wěn)定的,我們應(yīng)著手于日常的治安管理,做好日常的基層工作,做好日常的安全防范工作。如果那樣,我們的社會也將更加安寧。 自從1983年我國第一次開展“嚴(yán)打”行動以來,有關(guān)“嚴(yán)打’’利弊的爭論一直就沒有平息過,上述案例正是這種爭論的一個縮影。理論界對“嚴(yán)打”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即“反對說”和“反思說”,而相關(guān)部門對“嚴(yán)打’’的看法較為一
某市“嚴(yán)打”3月重大案破案率100%是功績還是失職?① 據(jù)報載: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個月內(nèi)破獲各類刑事案件l 228起,打掉公安部掛牌的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4個、黑惡犯罪集團21個,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案率100%。讀后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想借貴報問一聲:這到底是功績還是失職? 眾所周知,黑社會性質(zhì)的犯罪集團和黑惡犯罪集團均非一日可成,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為什么我們的公安部門不能將其控制、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難道該市的這些集團都是在一天或一月內(nèi)形成的?再往下看,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該市公安局實行了民警破案獎懲制,每破一起掛牌案件,市政府獎勵20萬元,對有功民警獎勵2萬元,調(diào)動了民警的工作積極性。同時,對工作失職、打擊不力、出現(xiàn)失誤的民警嚴(yán)肅追究責(zé)任云云,并羅列了一些被處分人員數(shù)字。我不明白:如果沒有上述獎勵,那些犯罪集團和犯罪人員是否仍會逍遙法外?我們的民警就會沒有工作積極性?我不明白,我們的民警拿著國家的俸祿,拿著人民警察的警銜津貼和行業(yè)風(fēng)險金,手握著刑事偵查、治安管理種種特權(quán),并享受著人民警察的美稱,為什么就沒有積極性了呢?在此之前,那些局長、主管領(lǐng)導(dǎo)平日里是否有失職之嫌?為什么能穩(wěn)穩(wěn)地待在領(lǐng)導(dǎo)崗位上? 一個法治的國家絕不應(yīng)是靠嚴(yán)打、專項治理這些運動來保持社會治安穩(wěn)定的,我們應(yīng)著手于日常的治安管理,做好日常的基層工作,做好日常的安全防范工作。如果那樣,我們的社會也將更加安寧。 自從1983年我國第一次開展“嚴(yán)打”行動以來,有關(guān)“嚴(yán)打’’利弊的爭論一直就沒有平息過,上述案例正是這種爭論的一個縮影。理論界對“嚴(yán)打”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即“反對說”和“反思說”,而相關(guān)部門對“嚴(yán)打’’的看法較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