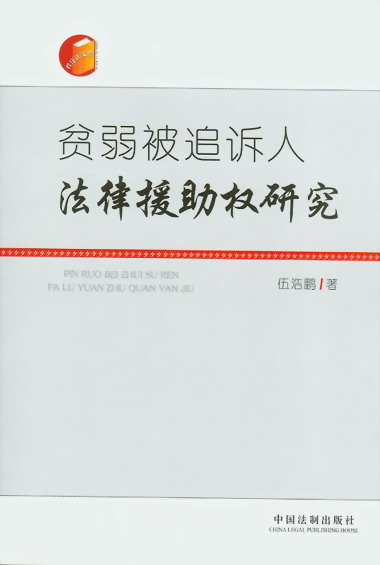 權利應當在現(xiàn)有的社會條件下設定,如果超越國家和社會所能承受的范圍,即使設置了內(nèi)容廣泛的權利,在實踐層面也將如同“鏡中花,水中月”。這就是權利的界限問題。權利的界限包括兩方面內(nèi)容:一是其立法時的界限,即哪些權利應當有,哪些權利不應有,哪些權利能夠有,哪些權利不能有①;二是指權利被法概括出來之后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運行的界限,即權利在什么時間、在什么范圍內(nèi)、對什么人能夠實現(xiàn)的界限,亦即法律上的保護力在多大程度上與人的價值相統(tǒng)一的界限②。此外,因為權利的行使主體是人,在被行使的過程中要受人的主觀意志的控制。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本性驅動,權利主體在行使權利時極有可能為了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突破權利的界限,從而造成對他人或社會利益的損害,這就產(chǎn)生了權利濫用的問題。有學者將權利濫用界定為:“權利人在權利行使過程中故意超越權利界限損害他人的行為。”③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同樣存在著權利界限及權利濫用的問題。 在權利界限方面,上文中講到了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內(nèi)容,通過賦予其各項權能,對其獲得并實現(xiàn)法律援助的權利提供了多元化的途徑,從而有助于貧弱被追訴人更容易地行使其權利。但是權利行使的便捷性,容易導致需求的無序增長,致使有限的國家資源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立法者出于盡量擴大權利主體利益保護范圍的初衷,無限制地放寬權利行使的條件,往往會導致超越國家資源的承受能力。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作為國家對貧弱被追訴人群體所提供的特殊救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如依據(jù)英國的《1988年法律援助法》,任何人只要通過了經(jīng)濟和案情審查,并能找到一名事務 律師為其代理,他就可以獲得法律援助。這種情況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一是無法控制法律援助經(jīng)費的增長,給國家財政造成極大的壓力;二是法律援助服務的質量參差不齊,使很大一部 分急需法律援助的人得不到優(yōu)質的服務;三是法律援助資金得不到有效利用,一些勝訴機會不大或不符合條件的案件獲得了法律援助④。在俄羅斯,法律并未對獲得法官、檢察官和偵查 機構指定法律援助制定任何實質性標準(經(jīng)濟狀況),對于個人能否支付法律服務費用不存在任何審查。這樣實際上在所有 案件中都可以適用強制辯護。在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背景下, 由于缺乏足夠經(jīng)費的支持,難以保障被追訴人獲得高質量的法 律服務②。 權利濫用,這一原則雖然是為了抑制民法上個人權利的極度膨脹而創(chuàng)設出來的,但筆者認為,其對權利的規(guī)制作用對權利體系架構具有重要意義,它應當適用于整個法律體系,對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研究也同樣如此。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主體擁有多項權能,這意味著其能夠主動尋求國家的救濟。但是,如果不予以有效規(guī)制,就很難避免權利主體在行使權利時的隨意性,甚至是惡意性。有學者指出,“國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濟越多,發(fā)生道德公害和欺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是因為時間一長社會習慣就形成了,人們又以此界定什么是‘正常的’。這樣,對福利救濟的嚴重依賴就不再被認為是依賴,而變成了‘預料中的’行為。”①因為權利主體通常只會考慮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會考慮甚至有意忽略其行為將會導致的對他人以及社會利益的損害,而一旦達到故意損害他人利益的程度就構成了權利的濫用。所以有學者在界定權利濫用時,認為“權利乃法律分配一部分社會利益于權利人行使權利之結果,固不免使他人發(fā)生損害,然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的,則屬權利之濫用。”②可以說,“權利濫用的主觀方面是權利人損人利己的故意。”③司法實踐中,此類情況日益增多,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同樣如此,已經(jīng)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在荷蘭出現(xiàn)了當事人和律師都在濫用法律援助的現(xiàn)象。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調(diào)查表明,在所有批準的情形中,有18%是不甚明確和不甚規(guī)范的⑧。荷蘭針對上述情況建立了法律援助委員會,通過他們職業(yè)化地管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批準程序。現(xiàn)在荷蘭批準法律援助案件的不確定率低于3%,未確證(可能錯誤利用法律援助)的案件率已經(jīng)遠遠低于1%⑨。我國香港地區(qū)對此類問題也作出了限制,“在某些情況下,如申請人曾多次就同一事項申請法律援助,而其行為已屬濫用法律援助署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務,有關職員便會把案件轉交法律援助署署長,由署長根據(jù)《法律援助規(guī)例》第ll條所賦予的權力,向申請人發(fā)出命令,在未來最多三年內(nèi),不會考慮由申請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請。”① 對于權利行使過程中出現(xiàn)的突破權利界限及權利濫用問題,在對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制度構建中應當予以重視。控制權利的界限主要應當由立法機關負責,由其權衡利弊通過政治選優(yōu)法選擇何種權利應當并且適合在立法中予以保護。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必要性勿庸置疑,關鍵在于立法機關應當考慮投入多少司法資源對這一群體進行保護,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才是合理的。而控制權利濫用的責任則應當由國家及權利主體共同承擔。國家應在提供法律援助的條件設置上予以明確規(guī)定,并進行嚴格的審查,對濫用法律援助權的行為應有相應的懲罰措施;權利主體則要進行自我約束。對于突破權利界限及權利濫用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各國的普遍做法,是通過為貧弱被追訴人設置相應義務來實現(xiàn)的。貧弱被追訴人應當承擔的義務包括:(1)真實申請的義務,即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供個人真實的經(jīng)濟情況及案件情況;(2)不得隨意放棄和取消法律援助項目的義務,上文中已有分析,在此不贅述;(3)不得濫用法律援助資源的義務,受援人應當積極有效配合,盡量減少對資源的浪費;(4)隨時報告情況變化的義務,受援人應當及時將自身情況及案件情況的變化報告給法律援助機構。總之,對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規(guī)范,既重視其全能設置,有要關注其義務限制,只有在國家、社會、個人利益和諧意志的基礎上配制權利,才能使之成為真正有效的權利。
權利應當在現(xiàn)有的社會條件下設定,如果超越國家和社會所能承受的范圍,即使設置了內(nèi)容廣泛的權利,在實踐層面也將如同“鏡中花,水中月”。這就是權利的界限問題。權利的界限包括兩方面內(nèi)容:一是其立法時的界限,即哪些權利應當有,哪些權利不應有,哪些權利能夠有,哪些權利不能有①;二是指權利被法概括出來之后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運行的界限,即權利在什么時間、在什么范圍內(nèi)、對什么人能夠實現(xiàn)的界限,亦即法律上的保護力在多大程度上與人的價值相統(tǒng)一的界限②。此外,因為權利的行使主體是人,在被行使的過程中要受人的主觀意志的控制。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本性驅動,權利主體在行使權利時極有可能為了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突破權利的界限,從而造成對他人或社會利益的損害,這就產(chǎn)生了權利濫用的問題。有學者將權利濫用界定為:“權利人在權利行使過程中故意超越權利界限損害他人的行為。”③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同樣存在著權利界限及權利濫用的問題。 在權利界限方面,上文中講到了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內(nèi)容,通過賦予其各項權能,對其獲得并實現(xiàn)法律援助的權利提供了多元化的途徑,從而有助于貧弱被追訴人更容易地行使其權利。但是權利行使的便捷性,容易導致需求的無序增長,致使有限的國家資源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立法者出于盡量擴大權利主體利益保護范圍的初衷,無限制地放寬權利行使的條件,往往會導致超越國家資源的承受能力。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作為國家對貧弱被追訴人群體所提供的特殊救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如依據(jù)英國的《1988年法律援助法》,任何人只要通過了經(jīng)濟和案情審查,并能找到一名事務 律師為其代理,他就可以獲得法律援助。這種情況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一是無法控制法律援助經(jīng)費的增長,給國家財政造成極大的壓力;二是法律援助服務的質量參差不齊,使很大一部 分急需法律援助的人得不到優(yōu)質的服務;三是法律援助資金得不到有效利用,一些勝訴機會不大或不符合條件的案件獲得了法律援助④。在俄羅斯,法律并未對獲得法官、檢察官和偵查 機構指定法律援助制定任何實質性標準(經(jīng)濟狀況),對于個人能否支付法律服務費用不存在任何審查。這樣實際上在所有 案件中都可以適用強制辯護。在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背景下, 由于缺乏足夠經(jīng)費的支持,難以保障被追訴人獲得高質量的法 律服務②。 權利濫用,這一原則雖然是為了抑制民法上個人權利的極度膨脹而創(chuàng)設出來的,但筆者認為,其對權利的規(guī)制作用對權利體系架構具有重要意義,它應當適用于整個法律體系,對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研究也同樣如此。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主體擁有多項權能,這意味著其能夠主動尋求國家的救濟。但是,如果不予以有效規(guī)制,就很難避免權利主體在行使權利時的隨意性,甚至是惡意性。有學者指出,“國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濟越多,發(fā)生道德公害和欺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是因為時間一長社會習慣就形成了,人們又以此界定什么是‘正常的’。這樣,對福利救濟的嚴重依賴就不再被認為是依賴,而變成了‘預料中的’行為。”①因為權利主體通常只會考慮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會考慮甚至有意忽略其行為將會導致的對他人以及社會利益的損害,而一旦達到故意損害他人利益的程度就構成了權利的濫用。所以有學者在界定權利濫用時,認為“權利乃法律分配一部分社會利益于權利人行使權利之結果,固不免使他人發(fā)生損害,然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的,則屬權利之濫用。”②可以說,“權利濫用的主觀方面是權利人損人利己的故意。”③司法實踐中,此類情況日益增多,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同樣如此,已經(jīng)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在荷蘭出現(xiàn)了當事人和律師都在濫用法律援助的現(xiàn)象。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調(diào)查表明,在所有批準的情形中,有18%是不甚明確和不甚規(guī)范的⑧。荷蘭針對上述情況建立了法律援助委員會,通過他們職業(yè)化地管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批準程序。現(xiàn)在荷蘭批準法律援助案件的不確定率低于3%,未確證(可能錯誤利用法律援助)的案件率已經(jīng)遠遠低于1%⑨。我國香港地區(qū)對此類問題也作出了限制,“在某些情況下,如申請人曾多次就同一事項申請法律援助,而其行為已屬濫用法律援助署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務,有關職員便會把案件轉交法律援助署署長,由署長根據(jù)《法律援助規(guī)例》第ll條所賦予的權力,向申請人發(fā)出命令,在未來最多三年內(nèi),不會考慮由申請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請。”① 對于權利行使過程中出現(xiàn)的突破權利界限及權利濫用問題,在對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制度構建中應當予以重視。控制權利的界限主要應當由立法機關負責,由其權衡利弊通過政治選優(yōu)法選擇何種權利應當并且適合在立法中予以保護。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必要性勿庸置疑,關鍵在于立法機關應當考慮投入多少司法資源對這一群體進行保護,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才是合理的。而控制權利濫用的責任則應當由國家及權利主體共同承擔。國家應在提供法律援助的條件設置上予以明確規(guī)定,并進行嚴格的審查,對濫用法律援助權的行為應有相應的懲罰措施;權利主體則要進行自我約束。對于突破權利界限及權利濫用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各國的普遍做法,是通過為貧弱被追訴人設置相應義務來實現(xiàn)的。貧弱被追訴人應當承擔的義務包括:(1)真實申請的義務,即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供個人真實的經(jīng)濟情況及案件情況;(2)不得隨意放棄和取消法律援助項目的義務,上文中已有分析,在此不贅述;(3)不得濫用法律援助資源的義務,受援人應當積極有效配合,盡量減少對資源的浪費;(4)隨時報告情況變化的義務,受援人應當及時將自身情況及案件情況的變化報告給法律援助機構。總之,對貧弱被追訴人法律援助權的規(guī)范,既重視其全能設置,有要關注其義務限制,只有在國家、社會、個人利益和諧意志的基礎上配制權利,才能使之成為真正有效的權利。聲明:該書摘由本站掃描錄入,僅供介紹圖書使用,錯誤在所難免,引用時請與原書核對。
Copyright © 1999-2024 法律圖書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