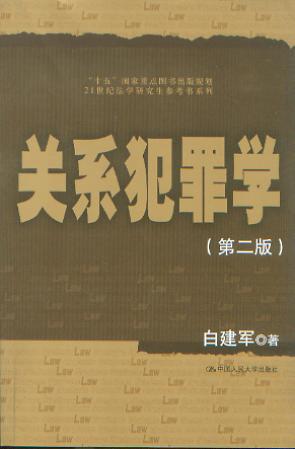
關系犯罪觀與控制社會控制
犯罪系研究是犯罪學的本體部分。在中篇里,將犯罪關系分解為四個方面的具體關系,即犯罪與秩序的關系、犯罪與被害的關系、犯罪與懲罰權的關系、犯罪與環境的關系。在這四對關系中,犯罪問題才能得到大體上比較全面、深刻的把握。
在犯罪與秩序的關系中,主要分析了犯罪特性的概念。所謂犯罪特性,也就是通常所謂的犯罪性,是指犯罪行為或者其行為傾向之所以受到社會譴責或拒斥的特別的內在根據。按照本能直覺主義,犯罪性的核心在于對倫理秩序的破壞,犯罪意味著倫理意義上的惡行。而按照環境經驗主義,犯罪性的核心在于其對社會秩序的違反,犯罪意味著社會秩序意義上的有害行為。這一章最重要的發現和推論是,所謂純粹的犯罪,即在任何層面都具有絕對犯罪性的犯罪并不多見,犯罪并不是某一類人特有的行為方式,社會各個階層都有各自特有的違法犯罪模式。所以,社會控制是所有人針對所有人的控制,每個人都應當是社會控制的主體,社會控制不應成為某些社會成員的專利。
在犯罪與被害的關系中,主要分析了犯罪形態的概念。所謂犯罪形態就是犯罪學理論的分析單位、刑事法律的評價對象以及犯罪性的客觀載體的總稱,或者說是犯罪相對于科學研究、控制實踐以及評價規范而言的存在方式。罪行中心主義認為犯罪行為是基本的犯罪形態,而罪人中心主義則認為犯罪人才是基本的犯罪形態。筆者認為,犯罪互動是同時包容了罪行與罪人且更接近犯罪實際的犯罪學范疇。犯罪學的研究焦點應當實現從犯罪中心(罪行中心及罪人中心)向犯罪互動中心的轉移。最原始的犯罪互動在較大程度上是集體加害與集體被害之間的互動,因而更容易表現出概括的、象征性的攻擊性。隨著社會的進步,集體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再是犯罪互動的基本屬性。這個變化首先發端于社會關系的多元化,人們之間不再簡單劃分為不同集體的人,犯罪逐漸被視為個人之間的沖突。因此,國家應當逐漸從沖突關系中游離出來,對犯罪的懲罰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中立的立場。
在犯罪與國家懲罰權的關系中,主要分析了犯罪定義的概念。犯罪定義是指一套符號體系和規范準則,這套符號和規范被用來指稱那些需要被冠名為犯罪的行為,并賦予這些行為以犯罪的意義和屬性,從而彰顯一定的主流價值取向,因而又是記錄犯罪化過程的符號體系和規范準則。對此,主體本位的犯罪定義觀認為,犯罪定義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定義者,即定義的主體,主體性是犯罪定義的核心屬性。這是能動論、多元論以及沖突論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而客體本位的犯罪定義觀認為,犯罪定義中的決定性因素是被定義的行為、現象本身,客體性是犯罪定義的核心屬性。客體本位的犯罪定義觀的理論基礎是摹狀論、一元論和自然論。如果堅持客體本位的犯罪定義觀,犯罪就是自在的,獨立于定義主體而存在的事物。犯罪定義主體只能發現犯罪,而不能發明犯罪。如果堅持主體本位的犯罪定義觀,犯罪則是被按照一定需要和標準塑造出來的事物。筆者認為,主體性的確是在何種行為應當被犯罪化的過程中表現最為活躍的因素,這就使得犯罪定義有可能成為犯罪定義主體濫用規范優勢的工具。然而,犯罪定義實際上是主客體之間的一個中介物,因此,只有在主客體之間的互動中調整自己,既服從來自主體方面的規定,又接受來自客體方面的制約,犯罪定義才能避免主體性的恣意放大。犯罪定義并不當然是關于犯罪的指稱,因此,控制犯罪,必須在不斷的試錯過程和實證分析中自覺對犯罪定義過程進行科學控制。
在犯罪與環境的關系中,著重分析了犯罪規律的概念。對此,犯罪學中有因果中心說和概率中心說兩種理解。在比較兩說的基礎上,筆者將犯罪規律理解為經實證檢驗證實的犯罪現實中普遍的本質聯系。犯罪的出現、運動、改變和消失,都要受制于這些本質聯系的作用。人們可以利用犯罪規律為自己服務,但不可制造、消滅、改變犯罪規律,更不能杜撰犯罪規律。犯罪規律本身是客觀的,但其形式又是主觀的。在犯罪規律研究中,沒有理論的實證數據就像沒有放鹽的菜肴,再豐富、再好看也沒有味道;沒有實證檢驗和實際數據的理論就像是方向或制動隨時會失靈的汽車,可以跑得很快,但不可靠;而沒有體系或思維框架的理論或數據,就如同被放大1 OOO倍的美女臉上的一個汗毛孔,雖然真實可靠,但一點兒也不好看,是一種過于真實的失真。當然,目前更為突出的問題是馬路上跑的不可靠的“汽車”太多,而標準的實證分析鳳毛麟角。于是,筆者詳細討論了如何發現、證實犯罪規律的實證分析方法,以及13種具體犯罪規律及其利用。從這一章的分析中也可以導出一個理念:既然犯罪要受制于犯罪規律,那么,社會控制實踐必須遵循、服從、接近、符合犯罪的客觀規律。任何針對犯罪的社會控制都只能是有限的社會控制。
在這四個部分中,不論是犯罪與秩序的關系、犯罪與被害的關系、犯罪與權力的關系,還是犯罪與環境的關系,其共性都是關系,所以,犯罪關系是最高層次的犯罪學范疇,對犯罪關系的研究構成了犯罪學的理論本體。作為這個理論本體的展開,四個犯罪學核心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是:犯罪特性是犯罪形態的實質內容,有什么樣的悖德性或危險性,就有什么樣的罪行、罪人或犯罪互動。而犯罪形態則是犯罪特性的表現形式,一定的犯罪特性可以通過不同的罪行、罪人或加害——被害關系表現出來。所以,犯罪特性和犯罪形態共同構成了犯罪存在本身。進一步看,作為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犯罪存在又同時作為犯罪化的客體和犯罪規律研究的認識對象存在著。從這個意義上說,犯罪關系實際上是犯罪與社會之間的一種主客體關系,其中,客體就是由犯罪特性和犯罪形態共同構成的所謂犯罪存在,主體就是針對犯罪存在而從事犯罪化活動與犯罪規律研究的實踐者和認識者。所以,犯罪關系又是主客體之間認識與被認識、反映與被反映、評價與被評價、實踐與被實踐、塑造與被塑造的互動關系。在這個互動關系中,一方面,主體針對犯罪存在的犯罪化實踐活動必然對犯罪存在本身構成一定影響。另一方面,犯罪存在的變化又反過來反映在主體的頭腦中。所以說,犯罪關系是個動態的結構,其中主客體之間實踐關系和認識關系的不斷循環往復,構成了完整的犯罪關系。犯罪關系是犯罪問題的客觀邏輯,或者反過來說,犯罪問題的客觀邏輯的犯罪學表達,就是犯罪關系。可見,犯罪從來都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即使作為認識對象,犯罪身上也含有認識者的痕跡。因為認識者同時又是定義者、實踐者,其定義過程和實踐過程或多或少都會塑造、改變著犯罪。當犯罪被這樣理解和把握時,其本質就不是一個“惡”字可以概括得了的。犯罪是一種客觀、自然的、被我們能動的定義活動所塑造出來的惡害。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社會,一個文明,一種文化,對待犯罪問題的基本態度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對待自己的基本態度。關于犯罪關系的上述概括,是繼儲槐植教授提出關系犯罪觀之后,對犯罪關系問題即犯罪學本體研究的一種理論推進,使關系犯罪觀的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深化和發展。
一個忠實反映犯罪問題客觀實際的理論體系,應該同時表現出強大的理論張力。否則,人們還是無法借助這個體系認識到犯罪問題的深刻本質。對上述每個關系的分析,最終都引導我們來到社會控制的某個層面。社會控制就寓于犯罪關系的主客體結構中(這里的社會控制,當然是指針對犯罪的社會控制,而非廣義上的整個社會生活的社會控制),社會控制是犯罪關系的必然邏輯結果。進一步看,當把這些層面的社會控制歸納起來便發現,由犯罪關系結構推導出來的社會控制,應當是科學反映犯罪關系,也即得到理性控制的社會控制,控制社會控制的客觀基礎就源自于犯罪關系本身的客觀要求。換句話說,犯罪關系的控制,就是社會控制的控制;社會控制的控制,也就是犯罪關系的控制。在2002年第2期的《中外法學》上,筆者曾經撰文提出“控制社會控制”的說法。但在當時,這個結論并不是從犯罪關系推導出來的,而主要是基于互動論的原理所引申出來的。按照互動論,社會控制并不是當然地遏制犯罪,甚至可能制造犯罪,所以,控制社會控制就應當是犯罪問題的解決思路之一。當時筆者所說的控制社會控制,核心的問題是對控制效果給予足夠的關注,而且強調,控制社會控制并不是要廢除社會控制,更不是摧毀現存的社會控制,而是完善社會控制,不間斷地根據控制效果調整控制行為,更有效地實現社會控制的目標。在該研究中,筆者將控制社會控制具體化為12個方面。現在看來,從不同的邏輯過程都能最終得出控制社會控制的結論,控制社會控制的結論既得到了互動論的支持,又與關系犯罪觀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可見,筆者完全有理由繼續完善、深化這一理念。
第一,從犯罪性分析中,筆者導出了“犯罪并非某類人特有的行為方式,每個社會人群都有自己可能的犯罪方式”,因此,“社會控制是人人對人人的控制,而非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專利”的結論。這就意味著,社會控制的控制,首先是對社會控制參與者的控制,是對社會控制權力壟斷的控制,是對這種壟斷可能導致的規范濫用的控制。第二,從犯罪形態分析中,筆者導出了“刑罰權的中立性”命題。這就意味著,社會控制的控制還是一種控制立場的控制,表現為調節被害人方面的責任負擔以控制犯罪。犯罪控制不是簡單地打擊犯罪,而是對加害——被害關系的調整。第三,從犯罪定義的分析中,筆者還導出了
“犯罪定義并不當然是關于犯罪的指稱,因此,控制犯罪必須自覺對犯罪定義過程進行科學控制”的結論。這就意味著,社會控制還可能是危險的社會控制,社會控制的控制還是控制者自身主體性的控制,表現為犯罪的客觀規定性對犯罪控制主體主觀意愿和能動性的控制。第四,從犯罪規律分析中,筆者還導出了“犯罪和犯罪控制都同樣受制于犯罪規律”的結論。這就意味著,社會控制都是有限的社會控制,犯罪控制主體不得不服從來自犯罪方面的客觀規律,科學規范自己的控制實踐。總之,這四個方面的社會控制都源自于一定的犯罪關系,而這些意義上的社會控制又都意味著社會控制的控制,所以,犯罪關系的控制說到底就是社會控制的控制,控制社會控制是犯罪控制的最高形式。在本書的下篇里,筆者將集中討論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犯罪被害預防等領域的社會反應。由于這些形式的社會反應分屬社會控制的不同層面,所以,控制社會控制的思想將貫穿始終。筆者將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這些領域中的社會控制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出自覺的自我控制加以實證檢驗。
摘自:白建軍著《關系犯罪學/第二版/21世紀法學研究生參考書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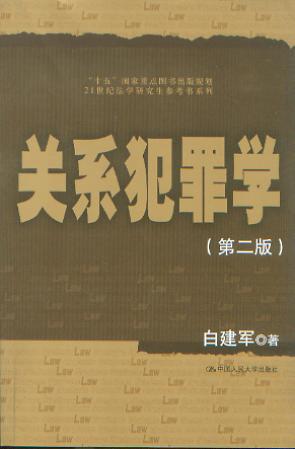 關系犯罪觀與控制社會控制
關系犯罪觀與控制社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