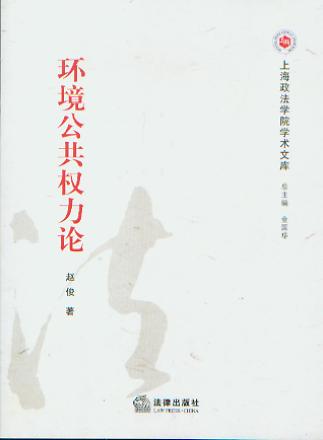
政府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合法性的標(biāo)準(zhǔn)
恩格斯說:“法權(quán)本身最抽象的表現(xiàn),即公平。”①羅爾斯也認(rèn)為:“正義的原則是一種公平的協(xié)議或契約的結(jié)果……‘作為公平的正義’這一名稱的性質(zhì):它示意正義原則是在一種公平的原初狀態(tài)中被一致同意的。”②正是出于對公平的珍視,羅爾斯確立了他的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平等自由的原則,第二個原則是機(jī)會的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的結(jié)合。其中,第一個原則優(yōu)先于第二個原則,而第二個原則中的機(jī)會公正平等原則又優(yōu)先于差別原則,③所以公平地分配社會權(quán)利和義務(wù)是政府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合法性的一個基本要求。
我們知道,法律是通過權(quán)利和義務(wù)配置實(shí)現(xiàn)社會利益的分配。在環(huán)境法中,政府公共權(quán)力必須要面對兩個基本利益,一個是經(jīng)濟(jì)利益,另一個是環(huán)境利益。政府公共權(quán)力如何在經(jīng)濟(jì)利益和環(huán)境利益的分配中保持其合法性,公平是一重要依據(jù)。而公平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公平分配利益的實(shí)質(zhì)就是如何公正地對待人的問題。
環(huán)境利益和經(jīng)濟(jì)利益的公平分配不僅要符合環(huán)境保護(hù)的目的,還要有利于法的價值目標(biāo)“秩序和效率”的實(shí)現(xiàn):這是一個十分復(fù)雜的問題。社會利益是諸多個人利益的總和,社會利益分配肯定會涉及個人利益問題,依據(jù)正義的要求,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在分配社會利益時,除了堅持公平原則外,還涉及“合作、效率和穩(wěn)固的問題”。在權(quán)力配置中,“個人的計劃就需要相互調(diào)整,以使它們的活動和衷共濟(jì)并都能貫徹到底,不使任何合法的愿望受到嚴(yán)重挫折……而且,這些計劃的實(shí)行應(yīng)當(dāng)導(dǎo)致以有效率的和與正義一致的方式實(shí)現(xiàn)一定的社會目標(biāo)。最后,社會合作的計劃必須是穩(wěn)定的。它必須多少有規(guī)律地被人們遵循,它的基本規(guī)范自動地起作用,一旦有違反的現(xiàn)象產(chǎn)生,穩(wěn)定的力量就應(yīng)出來防止進(jìn)一步的違反和促進(jìn)原來安排的恢復(fù)”。①法律就是一種穩(wěn)定的社會合作,它的基本規(guī)范自動地起作用,一旦有違反的現(xiàn)象產(chǎn)生,穩(wěn)定的力量就會來防止進(jìn)一步的違反和促進(jìn)原有安排的恢復(fù),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作為有計劃的環(huán)境管理和控制手段,其基本功能是在環(huán)境領(lǐng)域促成穩(wěn)定的社會合作,并對這種合作按照利益平衡的原則進(jìn)行適當(dāng)?shù)陌才拧?br>
所以說公平、效率和穩(wěn)定都與正義問題相聯(lián)系。“缺少某種統(tǒng)一有關(guān)正義與非正義意見的標(biāo)準(zhǔn),個人要有效地協(xié)調(diào)它們的計劃以保證堅持那些相互有利的安排顯然就會困難得多……既然正義觀的特定作用方式就必然要影響到效率、合作和穩(wěn)定的問題。一般來說,我們不可能僅僅通過一種正義觀在分配方面的作用來把握它,不管這種作用在辨識正義的概念是多么有用。我們必須考慮它的更為寬廣的聯(lián)系,因?yàn)椋词拐x有某種優(yōu)先性,是制度的最重要價值,下面這種說法也還是正確的: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種正義觀比另一種正義觀更可取,是因?yàn)樗母鼜V泛的結(jié)果更可取。”
因此,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合法性的實(shí)現(xiàn)要同時考慮到公平、效率和穩(wěn)定的正義標(biāo)準(zhǔn)。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說,在一定時期,由于社會發(fā)展現(xiàn)實(shí)的決定,這三個標(biāo)準(zhǔn)的優(yōu)先性有先后之分,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種正義觀比另一種正義觀更可取是因?yàn)樗母鼜V泛的結(jié)果更可取。從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狀來看,為什么環(huán)境利益在一定意義上要優(yōu)先于經(jīng)濟(jì)利益,主要原因就是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是人類的長遠(yuǎn)利益,沒有了環(huán)境這個基本的生存條件,人類的未來是不可想象的——環(huán)境利益所代表的正義觀具有更廣泛的結(jié)果。
環(huán)境正義觀兼顧到了效率、合作和穩(wěn)定三方面的因素。
從效率的角度講,環(huán)境正義觀,是經(jīng)濟(jì)利益得以實(shí)現(xiàn)的前提,沒有基本的環(huán)境條件,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僅是沒有效率的也是不可能的,其結(jié)果就是所謂“沒有發(fā)展的增長”。
從合作的角度講,堅持環(huán)境正義觀,客觀上促進(jìn)了國際間合作、區(qū)域間的全面合作,自然環(huán)境的整體性的特點(diǎn)要求人類在發(fā)展過程中必須進(jìn)行必要的合作,否則持續(xù)發(fā)展就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急劇擴(kuò)大的交往空間對環(huán)境合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們再也不是亞當(dāng)·斯密時代所描述的那種情形了:“無論我們?nèi)绾侮P(guān)心那些我們不熟悉或者沒有聯(lián)系的人們的命運(yùn),他們完全處于我們的行動波及的范圍以外,這種興趣只能產(chǎn)生對于我們自己的焦慮,而對于他們沒有任何益處。我們有什么理由為了月球上的社會擔(dān)心?所有人,甚至是那些距離最遙遠(yuǎn)的人們,無疑問應(yīng)該得到我們善良的祝福,我們自然給予他們善良的祝福。可是,盡管如此,如果他們是不幸的,使我們自己陷入焦慮無論如何不是我們的義務(wù)。因此,我們只能極少地關(guān)注那些我們既不能為之服務(wù)也不能傷害的人們的命運(yùn),他們無論在哪一個方面距離我們都是如此遙遠(yuǎn),似乎是由自然巧妙地安排的;如果有可能在這個方面改變我們環(huán)境的最初構(gòu)成,這種改變也會使我們一無所得。”(D很顯然,現(xiàn)代社會已不同于古典時代,由工業(yè)生產(chǎn)的全球急速擴(kuò)張和自然環(huán)境的整體性特征決定,不僅地球上所有的人類活動都彼此相關(guān),就連人類在地球之外的活動也相互聯(lián)系,任何空間的任何不利于環(huán)境的人類活動都可能構(gòu)成全球性的環(huán)境損害,所以國際社會在環(huán)境保護(hù)領(lǐng)域必須加強(qiáng)合作。
從穩(wěn)定的角度講,環(huán)境正義觀要求兼顧到不同發(fā)展階段的階層的不同利益。我們知道,人的需求是多樣性的,美國心理學(xué)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將人的需求依次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生理需要是人的最低層次的需要,只有當(dāng)這種需要得到滿足后,才會產(chǎn)生其他層次的需要。眾所周知,發(fā)展的不均衡性,使一個國家內(nèi)不同區(qū)域的發(fā)展程度不盡相同,這就決定了不同區(qū)域人們的需要的多樣性。到目前為止,一些地區(qū)人們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生存的需求仍是其最迫切的需求,只有這種需要得到滿足后,才可能涉及安全需求的問題。環(huán)境保護(hù)是人的一種安全需求,這種需求必須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后才能實(shí)現(xiàn)。但是由于環(huán)境問題日益嚴(yán)重,所以,如果不進(jìn)行環(huán)境保護(hù),人類長遠(yuǎn)的生存將受到威脅;另外,對一些溫飽問題尚未得到解決的地區(qū),生存利益是首要利益,如不允許這些地區(qū)發(fā)展經(jīng)濟(jì),當(dāng)下的生存就要受到嚴(yán)重的威脅,如果強(qiáng)行要求這些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利益服從環(huán)境利益不僅是不人道的,也是一個重大的不穩(wěn)定因素,是對正義原則的違背。我們知道,從長遠(yuǎn)來看,人類整體利益要高于地方區(qū)域利益,但要求較小的利益服從較大的利益并不是正義原則的要求,甚至還會違背正義原則,根據(jù)這種理由制定的法律也是不合法的。這是因?yàn)椤懊總€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義否認(rèn)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dāng)?shù)模怀姓J(rèn)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bǔ)償強(qiáng)加于少數(shù)人的犧牲。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quán)利絕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quán)衡”。①所以說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環(huán)境保護(hù)需要區(qū)域間和國家間全面合作;另一方面,犧牲少部分人的利益而照顧整體利益又會違正義原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全面推行生態(tài)補(bǔ)償制度。生態(tài)補(bǔ)償制度要求對因環(huán)境保護(hù)生存利益受損的群體和區(qū)域進(jìn)行充分、及時的利益補(bǔ)償,以實(shí)現(xiàn)環(huán)境保護(hù)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雙贏”的結(jié)果。這不僅有利于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還確保了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的合法性。
摘自:趙俊著《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論/上海政法學(xué)院學(xué)術(shù)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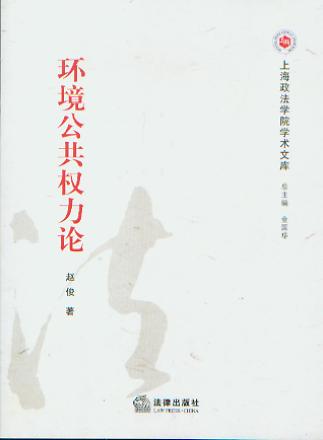 政府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合法性的標(biāo)準(zhǔn)
政府環(huán)境公共權(quán)力合法性的標(biāo)準(zhǔ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