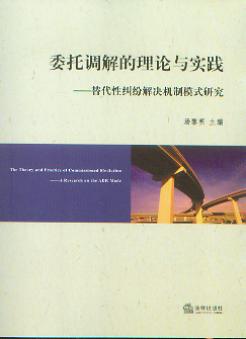
對策分析:進一步發揮人民調解組織在糾紛化解中的基礎性作用
如何進一步發揮人民調解組織在糾紛化解中的基礎性作用,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從立法層面來說,需要出臺一部《人民調解法》,以提升人民調解組織在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明確一些基本性的概念、原則和操作方式。從操作層面來說,需要加強人民調解的組織建設、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建立健全對人民調解工作的保障機制,司法行政機關和法院也要進一步加強對人民調解組織的業務指導。筆者無法對此一一展開論述,只就幾個關鍵性的問題提出一些管見。
(一)性質還原,厘清人民調解組織與公權力的關系
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經分析了,從靜態角度出發,可將糾紛解決的類型分為國家解決、社會解決和個人解決三個層面,人民調解即屬于社會解決的范疇。在當代社會,社會解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經驗已經證明,單單依靠國家的力量去解決糾紛,試圖依靠公權力——司法權與行政權去大包大攬,不僅不能完全勝任糾紛解決的重任,而且容易將民眾不滿的矛頭集中到國家,從而危及國家的權威。而將一定的糾紛交予社會這個“生態系統”去“自我凈化”,有助于社會的平穩和諧,有助于樹立國家權威,也有助于降低社會管理的成本。誠然,在已經高度機械化、組織化的現代社會,人民調解組織的發展壯大和功能發揮肯定離不開行政權、司法權等社會公權力的支持和指導,但事物均有其相反的兩面,公權力如果對人民調解組織過度侵蝕,乃至將其統合或變相統合于國家真正的司法行政制度,就等于是在法院(或仲裁機關)之外再造一個“法院(或仲裁機關)”,這在行政倫理學、行政組織學和行政經濟學方面都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此,要進一步發揮人民調解組織在糾紛化解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應當還原人民調解組織民間性、自治性、自主性的本質,厘清其與公權力的關系。
還原人民調解組織的性質,關鍵是要在將來的人民調解立法中,界定不同層級的人民調解組織之間的關系。根據《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第10條的規定,現有的人民調解委員會事實上存在三個層級:村(居)委會的調解委員會、鄉鎮(街道)的調解委員會和跨區域的聯會調解委員會。①在這種“大調解”的格局中,一方面存在著以自治為基點的人民調解與跨地域的新型糾紛解決機制(如消費者協會、行業協會、市場化咨詢機構等)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鄉鎮(街道)一級的調解又具有行政或準司法的性質和特征,與基層村(居)委會的自治性調解存在明顯不同。②因此,在將來的人民調解立法中,應當對村(居)委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和鄉鎮(街道)一級的人民調解委員會作出不同的定位和程序設定。村(居)委會一級的人民調解委員會應嚴格定義為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同時在人員的選任、調解的程序、法律的適用等方面作出較為寬松的規定,不必過于追求專業化和規范化。而鄉鎮(街道)~級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可以與基層政府主持或資助的準行政或準司法的調解中心等機構統合,形成具有基層司法和法律服務功能的公益性、專業化的調解機構。
(二)功能拓展,對特定類型的糾紛實行調解前置
人民調解組織的社會治理功能和文化功能的發揮,實質上是一個隨著人民調解組織的逐步發展而不斷積淀的過程。在現階段,人民調解組織的功能拓展,主要是指要擴展人民調解組織解決糾紛的領域,亦即“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圍繞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圍繞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物業管理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妥善處置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關于人民調解組織受理糾紛的范圍,《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第20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民間糾紛,包括發生在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爭議的各種糾紛。”從上述規定來看,人民調解組織接受調解的糾紛類型是極其廣泛的。但是,該“規定”第6條同時規定了“當事人有自主決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終止調解的權利”。也就是說,在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否接受人民調解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愿。在當下“法治崇拜”異化為“法院崇拜”的社會法治大環境下,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民調解的性質和化解糾紛的能力還存在諸多懷疑和不信任,就很容易出現各級人民調解組織和人民調解員“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窘境。①
在域外,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規定了對特定類型的糾紛必須實行調解前置(或稱強制調解)。如日本《家事審判法》規定,涉及人事關系的案件由家庭裁判所管轄,調停為訴訟程序的必經階段。又如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定,下列案件在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1)不動產所有人或地上權人或其他利用不動產之人相互間因相鄰關系發生爭執者;(2)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發生爭執者;(3)不動產共有人間因共有物之管理、處分或分割發生爭執者;(4)建筑物區分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間因建筑物或其共同部分之管理發生爭執者;(5)因增加或減免不動產之租金或地租發生爭執者;(6)因定地上權之期間、范圍、地租發生爭執者;(7)因道路交通事故糾紛或醫療糾紛發生爭執者;(8)合伙人間或隱名合伙人與出名合伙人間因合伙發生爭執者;(9)配偶、直系親屬、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姻親、家長或家屬相互間因財產權發生爭執者;(10)其他因財產權發生爭執、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者。此外,離婚之訴、夫妻同居之訴、終止收養關系之訴等人事訴訟案件,在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②
我國是否也應當把人民調解設定為特定類型案件的前置程序?對這一問題學界存在爭論。反對者認為,對于某些不愿意調解的當事人,強制他們在獲得判決之前必須先進行調解,無疑是一種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在這種情況下,與其經過調解,不如直接進行訴訟,這樣也許更符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則。支持者則認為,本來拒絕將爭端訴諸調解的人一旦親身經歷了調解所發揮的作用,便會明白它的種種益處,據此可以使爭議在提起訴訟之前通過調解即獲得解決,并且可以維護雙方問的和諧關系;此外,通過調解解決糾紛客觀上也緩解了法院所面臨的壓力,因此,把調解設置為訴訟的必經階段是完全合理的。①筆者認為,是否應當對某些類型的案件實行調解前置,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這更取決于實證分析的結果:如果在調解過程中“被迫”接受調解的一方放棄對調解的對抗,并且與對方合意達成調解協議的可能性足夠大,那么把調解設置為訴訟的必經階段就符合效益原則;如果某些類型的糾紛更適宜采用調解方式解決,而不適用訴訟程序,那么在進入訴訟前嘗試通過調解解決此類糾紛就是合理的。我們傾向于認為,對某些特定類型的糾紛實行調解前置是可取的,在今后的人民調解立法中,可以作出類似規定。在現階段,將調解前置的糾紛類型限定在以下幾個方面:道路交通事故糾紛、醫療糾紛、家事糾紛、相鄰糾紛以及其他標的額較小的合同和財產權屬糾紛。
(三)權威提升,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力
作為人民調解組織調解案件的成果體現,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問題是人民調解制度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直接關系到人民調解組織權威的樹立。如果經人民調解所達成的協議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允許當事人任意反悔,則等于宣告人民調解所做工作的無效,不僅徒然浪費本已緊缺的糾紛解決資源,也將不斷侵蝕民眾利用人民調解解決糾紛的意愿。因此,羅干同志指出:“基層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要充分發揮審判職能,通過依法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支持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肖揚院長也指出:“各級人民法院要認真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通過對人民調解協議的審核認定,賦予調解協議生效判決的效力。”
法律上對人民調解協議效力的認識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曾規定,人民調解組織出具的合法調解協議,將被法院作為證據予以采用。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與該市司法局聯合行文規定,民間糾紛經過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協議后,由街道(鄉、鎮)司法調解中心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如當事人反悔后拒不履行協議,其中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法院應當對當事人在街道(鄉、鎮)調解中心達成的協議書進行審核,如協議不違反法律、法規,不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及社會公共利益,也無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決中支持協議條款。2002年7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全國第一個以規定形式確認了人民調解協議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的約定,具有合同效力。2002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明確了“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并由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調解協議”。但是,如前所述,筆者認為該司法解釋僅僅解決了法院在遇到類似案件時的法律適用問題,并沒有賦予人民調解協議約束糾紛雙方的力量(power),當事人仍然會因為種種理由(甚至沒有理由地)在達成調解協議后反悔,此時如果其中一方起訴到法院,法院仍然要按照法定的程序立案、排期、開庭、審理。
筆者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要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的效力。在具體的操作路徑上則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是在人民調解立法中,直接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力。當然,理論界有不同的觀點:(1)如果人民調解協議具有法律效力,等同于把執法的權能授予了一個群眾性基層自治組織,在理論上說不通;(2)調解協議是建立在當事人自愿基礎上的,如果強求當事人履行協議,必然同人民調解工作的本質特點與基本原則相悖;(3)多數調解人員文化水平較低,法律知識欠缺,調解協議內容的合法性可疑,如果強迫當事人履行,勢必損害法律的嚴肅性。筆者認為這些反對意見確有一定的道理。因此我們尋求第二種路徑: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設置一種迅捷、簡便的一種程序,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的效力:一是公證程序,即任何一方當事人均可以請求公證機關對調解協議進行公證,經過公證的人民調解協議當然具有強制執行力;二是考慮到公證的費用可能過高進而影響當事人的積極性,當事人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以特別程序對人民調解協議進行審核,法院經審核后認為該協議不違反法律、法規,不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及社會公共利益,也無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的,則以裁定的形式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力。當然,這些設想的最終實現有賴于得到立法的認可。
摘自:湯黎明著《委托調解的理論與實踐;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模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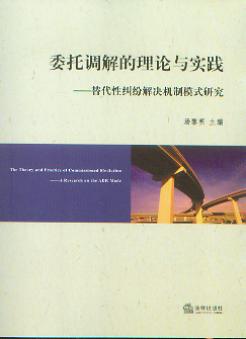 對策分析:進一步發揮人民調解組織在糾紛化解中的基礎性作用
對策分析:進一步發揮人民調解組織在糾紛化解中的基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