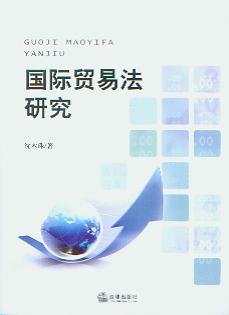
中國電子商務立法
自世界上出現(xiàn)電子商務之后,關(guān)于電子商務法之立與不立,如何立?我國便存在兩種甚至多種不同的意見。然任一意見都不存在是非對錯之區(qū)別,因它們均各自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實際、不同的認識基礎出發(fā),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如認為電子商務法當速立者,單項立法者,更多的是從國外的實際、國內(nèi)的發(fā)展需要著眼,并非要反對或摒棄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擾亂傳統(tǒng)法律基礎;認為電子商法當緩立者,甚至只主張修改現(xiàn)有法律,不主張單項立法者,則更多地著眼于將電子商務納入國內(nèi)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適用現(xiàn)行的法律秩序。但是,在不同意見的發(fā)表和討論中,卻往往出現(xiàn)了某種非此即彼的歸納和批評,影響或不利于學術(shù)的爭鳴與發(fā)展。
自1999年3月我國制定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下簡稱《合同
法》)以來,已沒有人能指責中國電子商務沒有立法,也沒有人會認為中國電子商務的前景不夠開闊;盡管當年中國的電子商務貿(mào)易額遠不足美國的萬分之一,電子商務立法也僅僅處在起步階段。相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問,卻都有人認為中國現(xiàn)有法律已足以使電子商務合同“進入實施階段”。⑩甚至有輿論認為中國電子商務的發(fā)展,將使中國在21世紀成為世界第二經(jīng)濟大國。外經(jīng)貿(mào)部也于2001年9月27日,在信息化工作會議提出了“10年內(nèi)企業(yè)電子商務應用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目標。⑩
中國電子商務國家層面立法最早的當屬《合同法》修改后,第11條關(guān)于書面形式包括“數(shù)據(jù)電文”及第33條關(guān)于當事人采用數(shù)據(jù)電文訂立合同可以“要求簽訂確認書”的規(guī)定。前者承認了電子合同的合法性,后者涉及電子合同生效的要件,可以說是對電子合同效力的一種探索。還有第16、26、34條規(guī)定了電子合同的要約時間、承諾時間及合同成立地點。但是,僅有以上條件,電子合同仍然無法操作,無法進入實施階段。
除國家立法原則上承認電子合同的法律地位,國務院及有關(guān)部委也制訂了一些行政法規(guī),如1994年2月18日國務院發(fā)布《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安全保護條例》,1996年2月1日國務院發(fā)布《計算機信息網(wǎng)絡國際聯(lián)網(wǎng)管理暫行規(guī)定》,1997年12月16日公安部發(fā)布《計算機信息網(wǎng)絡國際聯(lián)網(wǎng)安全保護管理辦法》,1998年2月13日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lǐng)導小組發(fā)布《計算機信息網(wǎng)絡國際聯(lián)網(wǎng)管理暫行規(guī)定實施辦法》,2000年9月25日國務院發(fā)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互聯(lián)網(wǎng)服務管理辦法》等。然而,這些規(guī)定一方面缺乏國家立法的權(quán)威性,另方面其內(nèi)容都局限于網(wǎng)絡的安全、管理等電子商務基礎設施的法律建設,并非對電子商務所涉主要問題的直接立法。
為解決電子合同實施過程中國家沒有對電子證據(jù)、電子簽字及電子認證等立法的問題,我國某些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先后制訂或頒布了一些規(guī)定,如廣東制定《對外貿(mào)易實施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暫行規(guī)定》,北京、上海加緊出臺電子商務法規(guī)等。這些地方立法雖然與美國各州的電子商務立法相比較在完整性、趨時性方面落后,但對當?shù)仉娮由虅瞻l(fā)展的促進作用不能低估,特別是其與國家對電子合同法律地位的原則性規(guī)定一起,起到了投“石”問路的作用。不過,以上地方立法最終也逃脫不了美國各州電子商務立法同樣的命運,即導致地區(qū)性差異,與電子商務的無區(qū)域性發(fā)生沖突。
我國2004年8月28日通過并頒布,2005年4月1日正式實施的《電子簽
名法》之前,中國電子商務立法除了以上既不全面完整,又不細致完善之外,還由于認識上和理解上的原因,導致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阻礙了電子商務的發(fā)展。
(一)“功能等同”演變?yōu)樾问降韧?br>
聯(lián)合國貿(mào)法會在擬定《示范法》過程中,曾考慮到各國現(xiàn)有法律對傳統(tǒng)貿(mào)易形式的諸多規(guī)定,建議采用“功能等同法”賦予電子商務與傳統(tǒng)商務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但不知是翻譯上還是理解上的原因,我國在制定《合同法》有關(guān)電子商務條款時,把這種“功能等同法”演變成為形式等同法,把無形的非紙質(zhì)的電子合同歸入有形的紙質(zhì)的“書面形式”。
《示范法》第6條writing(書寫)規(guī)定“當法律要求信息具有書寫功能時,一條數(shù)據(jù)信息如果包含的有關(guān)內(nèi)容可以被讀取并隨后使用,該信息應被視為符合該要求”。這里顯然是指電子合同賦有傳統(tǒng)合同同等的書寫功能,這是一種“假設”的功能等同,不是事實的功能等同,而且必須是“當”法律對數(shù)據(jù)信息有此要求的時候,并無任何要求將電子合同形式等同并歸人書面合同形式的意思,而早期我國學者在解釋《示范法》第6條時所持觀點是與《合同法》的形式等同法相一致的。⑩在這個問題上,似乎立法者與學界的觀點在相互影響。但由于我國學界早已習慣于一種聲音,因而長時間以來并未出現(xiàn)不同意見。其實,我們不必強制電子合同去作有違其實質(zhì)意義的“認祖歸宗”,無形的數(shù)據(jù)與有形的紙面,本就有實質(zhì)的不同,⑩而且聯(lián)合國貿(mào)法會制定《示范法》也曾認為可自行規(guī)定排除此項適用。
(二)電子簽名與“電子確認書”
電子合同歸入“書面形式”之后引起的第一個問題是電子簽名的效力和價值。電子簽名一詞是國際立法相對于書面簽名而提出來的,在修辭學上是一種借代法,它的表現(xiàn)形式是通過計算機網(wǎng)絡,借助數(shù)據(jù)信息完成的,它可以是數(shù)字,也可以是符號,與手書簽名委實沒有任何內(nèi)在聯(lián)系。但是,我國合同法還是避開了電子簽名的問題,提出另一種解決辦法,即“簽訂確認書”;這實際上是一種無意義的規(guī)避方法,因為簽字人通過數(shù)據(jù)信息交換簽訂確認書,卻仍無法繞開必須有確定身份的“電子簽名”這一問題,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的規(guī)定并不能使電子合同完成簽字人或依賴方認證的要求,而且按“書面形式”的規(guī)范,電子合同也根本無法擺脫手書簽名法律的束縛。
我國除了“書面形式”的合同要求當事人簽名之外,幾乎所有“書面形式”的票據(jù)也都要求有出票人的親筆簽名才能生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jù)法》(下簡稱《票據(jù)法》)第4條規(guī)定:“票據(jù)出票人制作票據(jù),應當按照法定條件在票據(jù)上簽章,并按照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jù)責任。持票人行使票據(jù)權(quán)利,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據(jù)上簽章,并出示票據(jù)。其他票據(jù)債務人在票據(jù)上簽章的,按照票據(jù)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jù)責任。”第7條規(guī)定:“票據(jù)上的簽章,為簽名、蓋章或者簽名加蓋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據(jù)的單位在票據(jù)上的簽章,為該法人或者該單位的蓋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權(quán)的代理人的簽章。在票據(jù)上的簽名,應當為該當事人的本名。”但是,在電子商務的交易過程中,完成交易的各方是通過無紙化的電子票據(jù)來進行支付和結(jié)算的,其“書面形式”是無法適用以上《票據(jù)法》要求的。
(三)電子證據(jù)與“視聽資料”
電子合同歸入“書面形式”之后引起的第二個問題是電子證據(jù)的價值和效力。電子證據(jù)是計算機內(nèi)存儲的無形的數(shù)據(jù)信息,其在訴訟中能否被法院采納作為證據(jù),我國《合同法》沒有規(guī)定,但按傳統(tǒng)的貿(mào)易法律和書面合同形式的證據(jù)要求,答案是否定的。因我國現(xiàn)行證據(jù)法規(guī)定,書面形式的證據(jù)必須是有形的書面文件(包括合同、單據(jù)),而且必須是“原件”,如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8條規(guī)定:“證據(jù)材料為復制件”在訴訟中不得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3條也規(guī)定:“收集、調(diào)取的書證應當是原件”,“收集、調(diào)取的物證應當是原物”。然而電子證據(jù)使用的是磁性介質(zhì),存儲的載體是計算機,其打印出來的“書面形式”委實不是“原件”,充其量也不過是“復制件”而已。
為此,多有學者主張把電子證據(jù)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63條規(guī)定的“視聽資料”類,有的甚至已經(jīng)提出電子證據(jù)認證辦法。④但是,我國“視聽資料”是必須依靠“其他證據(jù)”才能認定或產(chǎn)生效力的“間接證據(jù)”,如《民事訴訟法》第69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對視昕資料,應當辨別真?zhèn)危⒔Y(jié)合本案的其他證據(jù),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jù)”,可見這與《示范法》的規(guī)定大相徑庭。《示范法》第9條是明確不過地承認電子證據(jù)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在應用有關(guān)證據(jù)的任何規(guī)則時,不應否認其作為證據(jù)的可接受性。在電子商務交易中,電子數(shù)據(jù)存儲于計算機內(nèi),一般很難有除電子信息外的“其他證據(jù)”,當所有的電子證據(jù)都可能因沒有“其他證據(jù)”而失去效力時,還有誰敢用電子手段與中國做生意?如是,我國電子商務又如何能有長足發(fā)展或躋身于世界經(jīng)濟強國的希望?
(四)電子認證及技術(shù)標準
電子合同歸入“書面形式”引起的第三個問題是電子認證及其認證標準,即由誰認證及其依據(jù)的技術(shù)標準,這里面有一個人治或法治的問題。但在我國沒有對電子證據(jù)、電子簽名作出法律規(guī)定,又由于電子合同的“書面形式”引發(fā)一系列問題之后發(fā)生的電子商務糾紛,法官認證的標準和依據(jù)只能是傳統(tǒng)貿(mào)易法律的規(guī)定,而在傳統(tǒng)貿(mào)易法律根本不能適用電子商務這一新的貿(mào)易方式的情況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便可能無限制地擴大。這樣,一國之內(nèi)不同地區(qū)不同法官對同一證據(jù)的確認便可能完全不同。不少學者談到電子證據(jù)問題最后都不得不寄希望于法官“最大限度的公正”。然而,在沒有法律標尺的情況下,法官的公正只能是當事人的一廂情愿。如此,電子商務的法治便可能成為一句空話。為此,建立電子數(shù)據(jù)信息認證機構(gòu),制定統(tǒng)一的技術(shù)標準,修訂貿(mào)易法律的證據(jù)規(guī)定,是我國電子合同實施,電子商務發(fā)展的唯一選擇。
摘自:沈木珠著《國際貿(mào)易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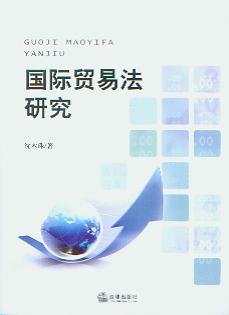 中國電子商務立法
中國電子商務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