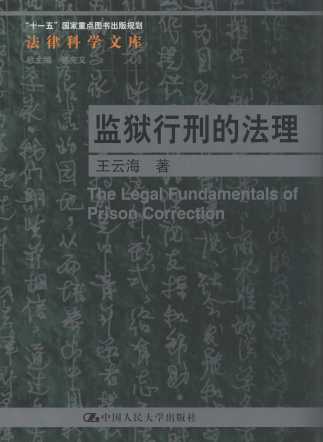
美國受刑人強制勞動的歷史
(1)初期階段的受刑人強制勞動
獨立革命前后,尤其是18世紀80年代,美國便開始了減少死刑、廢除身體刑,取而代之以拘禁刑的刑事司法改革運動。①然而,拘禁刑的導
人與推廣并非意味著刑罰從懲罰主義和一般預防主義完全轉(zhuǎn)向了改造更生主義和特別預防主義。當時的社會一方面認為無節(jié)度地適用死刑和身體刑本身過于殘酷,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僅僅將犯罪人拘禁于監(jiān)獄內(nèi)過于寬恕,應在拘禁之外設(shè)法進一步增大其痛苦。一些州的法律公然規(guī)定,對于受刑人應伴隨著重勞動(Hard Labor),以公然和侮辱性方法執(zhí)行刑罰。在這種思想下,強制勞動首先被作為加大受刑人痛苦的手段被采用和推廣,能否加大痛苦成為了強制勞動的主要標準和目的。同時,在此前提下,強制勞動也作為補足或支撐監(jiān)獄(以及看守所)所需費用的手段予以實施。也就是說,美國的受刑人強制勞動起初就具有作為“懲罰手段”和“榨取手段”的雙重性格。②
到了19世紀20年代,隨著拘禁刑的導人而設(shè)立的眾多的監(jiān)獄,無論
在獄內(nèi)管理方面還是在監(jiān)獄經(jīng)濟運營方面,都面臨失敗,單單淪為懲罰、暴動、傳播惡習的場所。面對這種情況,以基督教教會派教徒為中心展開了“改良監(jiān)獄”的運動。③基督教教會派教徒認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環(huán)境,在于犯罪人沒有能夠抵制環(huán)境影響的充分的宗教信仰,在于教會或家庭沒有能夠把犯罪人與不良環(huán)境隔開。基于這種犯罪觀,基督教教會派教徒主張,將犯罪人拘禁于監(jiān)獄的目的不應僅限于懲罰,而應該通過施高度的隔離和嚴格的紀律,通過宗教教育,促使其悔悟和反省,以此達到改造目的。為此,他們發(fā)明了一種稱作“懲治監(jiān)(Penitentiary)”的監(jiān)獄形態(tài)和制度,這種“懲治監(jiān)”在空間設(shè)計和時間分配上以受刑人相互間的高度隔離、嚴格的紀律、絕對的服從為基本原理;要求受刑人以圣書為伴,不得接觸其他任何東西。然而,同樣是基督教教會派教徒,卻在隔離的樣式、強調(diào)紀律的訓練還是強調(diào)自我反省等有關(guān)促使受刑人悔改的方法方面存在不同見解,最終形成了兩種不同形式的“懲治監(jiān)”。一種流行于賓夕法尼亞州,因此被稱為“賓夕法尼亞制”;另一種起源于紐約州的奧本一帶,因此被稱為“奧本制”。前者實行嚴格的獨房拘禁制,受刑人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只能一個人關(guān)押在房中,除圣書外不得接觸任何東西。后者實行夜間獨房拘禁,夜間朗讀圣書,白晝則集體從事勞動,勞動時必須保持沉默。“奧本制”由于允許或鼓勵受刑人勞動,所以具有經(jīng)濟意義上的優(yōu)勢,有利于監(jiān)獄實現(xiàn)“自給自足”,因此,除初期的賓夕法尼亞州之外,美國最終都轉(zhuǎn)向了“奧本制”。隨著“奧本制”的普及,受刑人的強制勞動也變得越來越普遍。到了19世紀60年代,通過受刑人勞動對受刑人實施經(jīng)濟榨取,以此實現(xiàn)監(jiān)獄的“自給自足”,甚至獲取更大的經(jīng)濟利益,成為了監(jiān)獄運營的主要目標和評價監(jiān)獄行刑的主要基準。(1)為此還“發(fā)明”了眾多的勞動方式②,其中包括“私業(yè)制(Personal Ac—count System)”(強制受刑人到親屬或社區(qū)經(jīng)營的企業(yè)或工地進行強制勞動)、“公業(yè)制”或“州業(yè)制(Public 0r State.Accotmt System)”(獄內(nèi)設(shè)立工廠或農(nóng)場,作為監(jiān)獄行刑的直接內(nèi)容直接組織受刑人勞動)、“包工制((;ontract Syst,em)”(受刑人的紀律及供給由監(jiān)獄負責,勞動理及產(chǎn)品販賣等包給民間企業(yè))、“出租制(Lease System)”(監(jiān)獄把受刑人完
全出租給民間企業(yè),從維持受刑人的紀律到勞動管理、產(chǎn)品的販賣等全部由民間企業(yè)負責)、“單價制(Piec}price System)”(受刑人的紀律、供給、勞動管理由監(jiān)獄負責,產(chǎn)品販賣包給民間企業(yè),監(jiān)獄和民間企業(yè)按販賣后的產(chǎn)品單價分紅)。
(2)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的受刑人強制勞動
以基督教教會派教徒為中心所展開的監(jiān)獄改良運動盡管在理念上提倡的是以宗教為基礎(chǔ)的“隔離、絕對服從和重勞動”三位一體的行刑原理,但現(xiàn)實中監(jiān)獄卻淪為了對受刑人實施殘酷虐待和進行經(jīng)濟榨取的場所,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批判。于是,美國監(jiān)獄協(xié)會于1870年發(fā)表了《辛辛那提宣言》,宣布行刑應堅持以治療為主的所謂“復歸社會”式理念,在此以后的100年間,美國在實踐中也大規(guī)模地推廣了這種“復歸社會”式行刑。隨著行刑理念的大轉(zhuǎn)變及“復歸社會”式行刑的展開,受刑人強制勞動在行刑中的地位也開始發(fā)生巨大變化,并非像過去那樣所有的受刑人或監(jiān)獄行刑的主要活動都必須集中在勞動上,相反,只有監(jiān)獄當局認為勞動對某個受刑人來講具有“治療”作用時,才作為“治療”的一個手段使受刑人從事勞動,大部分的受刑人或受刑人的大部分時間都不再從事勞動。當時美國監(jiān)獄的最大特征就是受刑人都處在“無為(Idleness)”狀態(tài)中,除了偶爾接受所謂的“治療”之外,整天無所事事。①
也就是說,受刑人勞動被降低為一種偶爾的治療手段,大部分的受刑人或受刑人的大部分時間被置于無所事事的狀態(tài)。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行刑理念的變化之外,還包括美國社會對受刑人勞動的態(tài)度的變化。隨著“懲治監(jiān)”時代“奧本制”的普及,監(jiān)獄行刑實際上變質(zhì)成了利用廉價勞動力及對受刑人予以榨取的活動。這樣就產(chǎn)生了受刑人勞動與民間企業(yè)勞動的沖突,民間企業(yè)認為,監(jiān)獄企業(yè)或利用受刑人勞動的民間企業(yè)實際上是在利用廉價勞動力進行不公平競爭(即所謂“民業(yè)壓迫論”);受刑人屬于“國家奴隸”或“法外之人”,他們沒有資格占取一般人的勞動機會;受刑人的勞動只能在民間企業(yè)沒有興趣的領(lǐng)域或不與民間企業(yè)發(fā)生沖突時才能被允許。為了滿足民間企業(yè)的這種要求,從19世紀70年代末起,美國一些州的議會便開始進行旨在限制受刑人勞動的所謂“限制立法”,禁止民間企業(yè)利用受刑人勞動。①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聯(lián)邦議會也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限制立法”,其中最為有名且至今仍然有效的法律有以下三個,即:“郝斯一庫珀法(The}lawes—Cooper Act,1934)”、“阿什斯特一薩默斯法(’Yhe AshtIrst—Summer‘s Act)”及“1940年法”。這些法律把監(jiān)獄產(chǎn)品或利用受刑人勞動制造的產(chǎn)品從州際貿(mào)易及其他國內(nèi)貿(mào)易中完全排擠了出去,對違反者科處嚴厲制裁。
面對嚴格的“限制立法”,美國的行刑當局試圖尋求妥協(xié),爭取在遵守上述“限制立法”的同時也能為受刑人保留一些勞動機會。為此,導人了一種被稱作“官用制”的制度。所謂“官用制(State-Use
System)”是指這樣一種制度:監(jiān)獄企業(yè)或利用受刑人勞動的民間企業(yè)不得將其產(chǎn)品投入一般市場,其銷售販賣對象只限于政府機關(guān),如果監(jiān)獄企業(yè)或利用受刑人勞動的民間企業(yè)能夠提供相應產(chǎn)品,政府機關(guān)應予以優(yōu)先采購。⑧
然而,盡管通過實施“官用制”,政府機關(guān)負有了優(yōu)先采購監(jiān)獄企業(yè)產(chǎn)品的義務,但由于政府機關(guān)的需求量很小,“官用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消除因“限制立法”而給監(jiān)獄企業(yè)及利用受刑人勞動力的民間企業(yè)造成的不利局面,“官用制”下的受刑人仍經(jīng)常處在“無為”狀態(tài)中,與受刑人勞動有關(guān)的監(jiān)獄企業(yè)等仍處在隨時被孤立和淘汰的困境中。
(3)20世紀70年代的受刑人強制勞動
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主張拋棄“復歸社會”理念的所謂“正義
模式”行刑一時成為熱潮,監(jiān)獄行刑實踐活動也因此發(fā)生了一些改變。正義模式論者認為,受刑人勞動既不具有任何“復歸社會”的治療作用,也沒有理由作為刑罰的懲罰內(nèi)容,具有和一般人的勞動一樣的性質(zhì);應視勞動為受刑人的權(quán)利,在此基礎(chǔ)上實現(xiàn)受刑人勞動的“正常化”,作為這種“正常化”的體現(xiàn),監(jiān)獄內(nèi)部應基于受刑人的“自我決定”和“自我責任”原則安排勞動,廢除勞動的強制,對勞動的受刑人給予工資;社會應視監(jiān)獄勞動與其他勞動一樣,對其同等對待,廢除眾多的“限制立法”,讓監(jiān)獄企業(yè)與其他企業(yè)同樣地參與市場,同樣進行競爭。①為了對應“正義模式”的這些主張,當時的美國對監(jiān)獄企業(yè)的政策作了一些調(diào)整。例如,一些州議會及聯(lián)邦議會修改了對監(jiān)獄企業(yè)實施的“限制立法”,有限度地允許監(jiān)獄企業(yè)的產(chǎn)品進入市場,也放寬了對民間企業(yè)雇傭受刑人的限制。另外,法院一方面判決受刑人不具有勞動權(quán),不具有領(lǐng)取工資的權(quán)利,但另一方面又指出,為了避免監(jiān)獄企業(yè)與民間企業(yè)之間因受刑人勞動的廉價性而形成不平等競爭,對進行了旨在營利的勞動的受刑人,應作為國家的恩賜支付最低工資。
(4)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受刑人強制勞動
然而,完全從受刑人權(quán)利角度看待行刑的所謂“正義模式”只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沒有真正成為支配美國行刑的主流理念。不僅如此,由于它過分強調(diào)“自我決定”和“自我責任”,反而給以主張最大限度減少行刑過程中的國家和社會的負擔為特征的新自由主義行刑論提供了部分理論基礎(chǔ),促成了新自由主義行刑論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美國的廣泛流行。②在新自由主義行刑論時代,美國的受刑人勞動首先是作為減少國家和社會對行刑的經(jīng)濟負擔,促使受刑人自己去履行對被害人的經(jīng)濟社會責任的手段而展開的。具體來講,受刑人勞動不再被作為促進受刑人復歸社會的手段,不再從實現(xiàn)對受刑人的改造等刑事法律角度予以運營;相反,受刑人勞動被完全視為一般的經(jīng)濟活動,完全按市場原理予以運營,促使受刑人積極參加勞動,向參加勞動的受刑人支付最低工資。與此同時,要求受刑人支付在監(jiān)獄的住宿費、伙食費、衣著費、勞動管理費甚至行刑費,也要求受刑人從勞動所得中支付對受害人的賠償?shù)荣M用。在這種運營方式之下,受刑人又重新被作為美國社會中最為廉價勞動力而被利用,曾盛行于19世紀的對受刑人的榨取的現(xiàn)象,在21世紀以后的美國又死灰復燃,受刑人又淪為了國家或社會的“奴隸”①。
為了能夠充分有效地利用受刑人的廉價勞動力,20世紀80年代以后
的美國監(jiān)獄主要采用了以下勞動方式②:1) “雇傭者模式(Employer
Model)”,即:民間企業(yè)作為雇傭者在自己經(jīng)營的企業(yè)內(nèi)以最低工資大量地雇傭受刑人,具體實施受刑人參與的經(jīng)營活動,全面負責產(chǎn)品制品在市場上的販賣,承擔有關(guān)企業(yè)的經(jīng)濟財政風險,作為雇傭者和經(jīng)營者直接享受雇傭受刑人進行經(jīng)濟經(jīng)營活動所獲得的經(jīng)濟利益。監(jiān)獄方面只負責監(jiān)獄秩序與保安。這種方式在當今的美國最為流行。2)“投資家模式(Inves—tor Model)”,即:民間企業(yè)只向監(jiān)獄所經(jīng)營的工廠、農(nóng)場等企業(yè)提供資金進行投資,但不直接參與其經(jīng)營活動,而監(jiān)獄方面既負責監(jiān)獄紀律和保安,又全面負責監(jiān)獄企業(yè)的經(jīng)營活動,按監(jiān)獄企業(yè)的盈利狀況向投資者提供經(jīng)濟回報。3)“顧客模式(Cllstomer。Model)”,即:民間企業(yè)只負責定期買取監(jiān)獄企業(yè)的產(chǎn)品,監(jiān)獄企業(yè)的經(jīng)營活動等都由監(jiān)獄方面負責。4)“管理型顧客模式((;ontrolling Customer Model)”,即:民間企業(yè)雖不直接擁有或經(jīng)營監(jiān)獄企業(yè),但作為產(chǎn)品的主要購買方對監(jiān)獄企業(yè)的經(jīng)營活動予以干涉,監(jiān)獄方面在這些企業(yè)的干涉指導下對監(jiān)獄企業(yè)進行管理經(jīng)營。5)“經(jīng)營模式(Managerial Model)”,即:民間企業(yè)派員負責指導和管理監(jiān)獄企業(yè)的經(jīng)營,為監(jiān)獄企業(yè)提供咨詢、技術(shù)及其他專門知識,無論監(jiān)獄企業(yè)經(jīng)營狀況如何都獲取經(jīng)營費用。6)“共同投資模式(Joint Ven—ture M()del)”,即:監(jiān)獄和民間企業(yè)共同投資于監(jiān)獄企業(yè),對其經(jīng)營活動進行共同管理,按投資比例共同分擔經(jīng)濟風險、分享企業(yè)利潤。
上述模式主要見諸美國各個州的監(jiān)獄系統(tǒng),而聯(lián)邦監(jiān)獄系統(tǒng)主要采取的是聯(lián)合獨立經(jīng)營方式。聯(lián)邦矯正局作為自己的外圍團體設(shè)立了稱作“聯(lián)邦監(jiān)獄產(chǎn)業(yè)機構(gòu)(UNICOR)”的經(jīng)營組織,聯(lián)邦矯正局通過各個監(jiān)獄當局負責監(jiān)獄的紀律和保安,該組織則專門負責聯(lián)邦監(jiān)獄所屬企業(yè)的經(jīng)管理活動,在下屬的五十多個聯(lián)邦監(jiān)獄中設(shè)立有一百多個工廠,大概20%的聯(lián)邦監(jiān)獄受刑人都受雇于這些企業(yè)。①
摘自:王云海著《監(jiān)獄行刑的法理/法律科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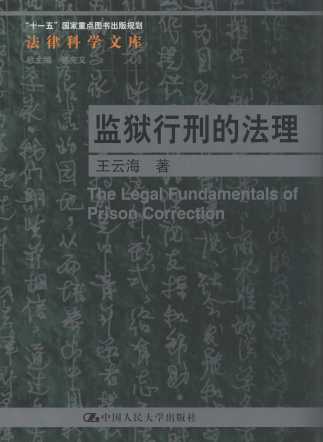 美國受刑人強制勞動的歷史
美國受刑人強制勞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