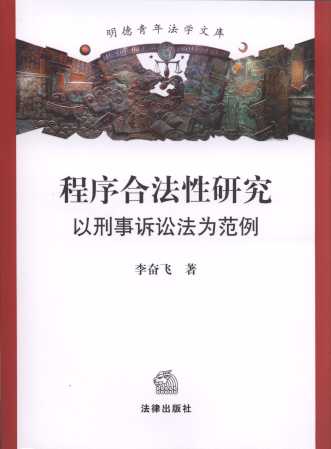
ŕP(guĘín)Ë┌í░│╠đ˛í▒Á─öÓ¤Ű(┤˙║ˇËŤ)íí
íííí╚š╣űËđ╚╦ćľ(wĘĘn)úČí░│╠đ˛í▒╩ă╩▓├┤?╬ĎÁ─╗ě┤┐╔Ďď╩ă:í░│╠đ˛í▒ż═╩ăí░╬ńøí▒íú├ŠîŽ(duĘČ)ĆŐ(qiĘóng)┤ˇÁ─ç°(guĘ«)╝ĎÖC(jĘę)øúȤŢ╚Ű└žż│Á─¤ËĎ╔╚╦íó▒╗ŞŠ╚╦▓╗âH┐╔ĎďË├ĂńĚ└˨úČ▀Ç┐╔ĎďË├Ăń▀M(jĘČn)╣ąíúŤ](mĘŽi)Ëđí░│╠đ˛í▒úČθ×Ú╚§Ň▀Á─éÇ(gĘĘ)╚╦├ŠîŽ(duĘČ)ç°(guĘ«)╝Ďîó▓╗┐░Ď╗ô˘íú
íííí╬ĎÁ─╗ě┤▀Ç┐╔Ďď╩ă:í░│╠đ˛í▒ż═╩ăí░ÖÓ(quĘón)└űí▒íú▓╗âHí░čo(wĘ▓)ÖÓ(quĘón)└űätčo(wĘ▓)│╠đ˛í▒(╝┤Í╗Ëđď┌╚╦Á─ÖÓ(quĘón)ĎŠ├Š┼R═■├{íó¤ŮÍĂ║═äâŐZÁ─ł÷(chĘúng)║¤úČďVďA│╠đ˛Á─ŻĘ┴ó▓┼ż▀ËđŇř«ö(dĘíng)đď)úČ°ăĎŤ](mĘŽi)Ëđ│╠đ˛▒úҤúČÖÓ(quĘón)└űîóđ╬═Č╠ôďO(shĘĘ)íú
íííí╬ĎÁ─╗ě┤ËÍ┐╔Ďď╩ă:í░│╠đ˛í▒ż═╩ăí░Ă┴Ҥí▒íú┐╔ĎďÎîĚĘ═ąÍ╗┐╝Ĺ]┼c▒ż░ŞËđŕP(guĘín)Á─╩┬îŹ(shʬ)║═ĚĘ┬╔úČ°▓╗Ë├╣▄í░╬ň░┘─ŕă░Á─┤║ă´┤ˇ┴xí▒║═í░╬ň░┘─ŕ║ˇÁ─Áěă˛╬úÖC(jĘę)í▒úČ▓╗Ë├╣▄ĚĘ═ą═ÔŤ░Ë┐Á─├˝ĎÔë║┴Ž║═«ö(dĘíng)ÖÓ(quĘón)Ň▀╩ăĚ˝ŁMĎÔíú
íííííşíş
ííííîŽ(duĘČ)Ë┌╬ĎÁ─╗ě┤úČ─│đę╦¨Í^í░â╚(nĘĘi)đđí▒Á─╚╦┐╔─▄đ─└´▓╗Ě■íú
ííííϲ?yĘĄn)ÚúČ╦űÁ─╦¨Ď?jiĘĄn)╦¨┬䪊ďV╦űúČí░│╠đ˛í▒ż═╩ăí░╩Í└m(xĘ┤)í▒íúËđĎ╗┤╬úČď┌═ÔÁěŇ{(diĘĄo)ĐđĽr(shʬ)úČËđĎ╗╬╗Ş▒Öz▓ýÚL(zhĘúng)ËH┐┌îŽ(duĘČ)╬ĎŇf(shuĘş):í░│╠đ˛▓╗ż═╩ăéÇ(gĘĘ)╩Í└m(xĘ┤)ćß?!í▒▀ÇËđĎ╗┤╬úČ║═Ď╗éÇ(gĘĘ)ĚĘîW(xuĘŽ)ă░Ţů═Č▄ç╗ě╝Ďíú┬Ě╔¤úČ╦űćľ(wĘĘn)╬Ď͸ϬĐđż┐╩▓├┤?«ö(dĘíng)╬ĎŇf(shuĘş)│÷í░đ╠╩┬│╠đ˛í▒Ľr(shʬ)úČ╦űÄÎ║§╩ă├ô┐┌°│÷:í░│╠đ˛ĚĘż═╩ă╩Í└m(xĘ┤)ĚĘí▒íú╝╚╚╗╩ăí░╩Í└m(xĘ┤)í▒úČ▓╗âHĎÄ(guĘę)ÂĘ▓╗ĎÄ(guĘę)ÂĘ▓ţäe▓╗┤ˇúČν╩ě▓╗ν╩ěĎ▓Ť](mĘŽi)ËđîŹ(shʬ)┘|(zhĘČ)ĎÔ┴xíú
íííí╦űÁ─╦¨ĎŐ(jiĘĄn)╦¨┬䪊ďV╦űúČí░│╠đ˛í▒Í╗╩ăí░▀^(guĘ░)ł÷(chĘúng)í▒íú╝╚╚╗╩ăí░▀^(guĘ░)ł÷(chĘúng)í▒úČ─┐Á─ż═╩ă×Ú┴╦┐┤ĂüÝ(lĘói)├└űÉúČ°▓ó▓╗ÍŞ═űĂń─▄ŇŠŇřŻÔŤQćľ(wĘĘn)ţ}íú╦¨ĎďúČËđÁ─░Ş╝■Űm╚╗═ąîĆ│Í└m(xĘ┤)ÁŻ╔ţĎ╣úČ▓ó╦óđ┬┴╦«ö(dĘíng)?shĘ┤)ěÁ─îĆ┼đÜv╩ĚúČůsĎ▓Ť](mĘŽi)Ëđ╩▓├┤ÍÁÁ├┘ŁďSÁ─íúϲ?yĘĄn)ÚúČ═ąîĆÍ╗╩ăÎ▀éÇ(gĘĘ)▀^(guĘ░)ł÷(chĘúng)úČÚ_(kĘíi)═ąÍ«ă░Â╝ĎĐŻŤ(jĘęng)Ëđ┴╦ŻY(jiĘŽ)Ňôíú╬Ďď┌═ÔÁěŮqÎo(hĘ┤)Á─Ď╗éÇ(gĘĘ)░Ş╝■Ď▓║▄─▄Ňf(shuĘş)├¸ćľ(wĘĘn)ţ}úČ«ö(dĘíng)╬Ďď┌Ú_(kĘíi)═ąă░░ĐŮqÎo(hĘ┤)ĎÔĎŐ(jiĘĄn)╠߯╗ŻoĚĘ╣┘Ľr(shʬ)úČĚĘ╣┘¤┬ĎÔÎR(shʬ)ÁěŇf(shuĘş):í░▀@éÇ(gĘĘ)░ŞÎË─ŃĎ▓θčo(wĘ▓)δŮqÎo(hĘ┤)░í?!í▒
íííí╦űÁ─╦¨ĎŐ(jiĘĄn)╦¨┬䪊ďV╦űúČí░│╠đ˛í▒ż═╩ăí░╣Ąż▀í▒íúĂń▓╗âH╩ăîŹ(shʬ)ČF(xiĘĄn)îŹ(shʬ)ˇwĚĘÁ─í░╣Ąż▀í▒úČËđĽr(shʬ)▀Ç╩ă▀M(jĘČn)đđ└űĎŠáÄ(zhĘąng)ŐZÁ─í░╣Ąż▀í▒íú2010─ŕ4ď┬15╚ŇÁ─íÂ─¤ĚŻÍ▄─ęíĚËđìłˇ(bĘĄo)Á└úČ▓╗âHś╦(biĘío)ţ}║▄đĐ─┐í¬í¬íÂí░▒╗Ëđδí▒▀Ç╩ăí░▒╗čo(wĘ▓)δí▒:ňXŇf(shuĘş)┴╦╦Ń?íĚúČâ╚(nĘĘi)╚ŢĎ▓║▄í░└Î╚╦í▒í¬í¬│đŮkďô░ŞÁ─ů^(qĘ▒)Öz▓ýď║Á─Öz▓ýÚL(zhĘúng)Ňf(shuĘş):í░Îą╚╦▓╗╩ă─┐Á─úČ─┐Á─ż═╩ăϬňXí▒íú╦¨ĎďúČď┌îŤ┬Ě┼Śë4600╚f(wĘĄn)ď¬Ĺ¬(yĘęng)╩Ň┐ţÁ─│đÍZĽ°Í«║ˇúČĎ╗îĆ┼đ╠Ä15─ŕËđĂ┌═Żđ╠Á─čč┼_(tĘói)╔╠╚╦ă˝─│Â■îĆ▒╗í░čo(wĘ▓)δßîĚ┼í▒íú
íííí╔§Í┴úČ╦űÁ─╦¨ĎŐ(jiĘĄn)╦¨┬ä▀ÇŞŠďV╦űúČí░│╠đ˛í▒ż═╩ăí░Ĺ═┴Pí▒íúϲ?yĘĄn)ÚúČí░│╠đ˛í▒Á─ćóä?dĘ░ng)Űm╚╗▓ó╬┤─▄îŹ(shʬ)ČF(xiĘĄn)îŽ(duĘČ)─│╚╦Á─ÂĘδúČÁź╩ăúČůsĂÁŻ┴╦îŽ(duĘČ)Ăń▀M(jĘČn)đđí░ŇĹěí▒íóí░Ĺ═┴Pí▒Á─θË├íú▒╚╚šúČÍěĹcí░┼Ý╦«ďŐ(shĘę)░Şí▒íó╔Ż╬¸í░ó╔Ż╬─░Şí▒íóŕâ╬¸í░ÍżÁĄÂ╠đ┼░Şí▒íó╔Żľ|í░Ş▀╠ĂżW(wĘúng)░Şí▒úČ▀@đę├¸´@î┘Ë┌ĐďŇôÎďË╔Ě«áâ╚(nĘĘi)Á─đđ×ÚúČď┌▒╗┐█╔¤í░ŇuÍrí▒Á─├▒ÎË║ˇúČ▒╗ËđŕP(guĘín)▓┐ÚTîĆËŹíóżđ▓Â─╦Í┴ĂďVíú
ííííď┘╚šúČÎď1996─ŕđŮŇř║ˇÁ─đ╠╩┬ďVďAĚĘîŹ(shʬ)╩ęĎďüÝ(lĘói)úČ╚źç°(guĘ«)޸ÁěŰm╚╗ËđöÁ(shĘ┤)░┘├ű┬╔Äčϲ?yĘĄn)Úí░đ╠Ě?06Ślí▒▒╗┴bĐ║íó┤■▓ÂíóĂďVúČ╚╗°ÎţŻKŻ^┤ˇÂÓöÁ(shĘ┤)┬╔ÄčÂ╝╬┤▒╗ŇJ(rĘĘn)ÂĘËđδíú
ííííËÍ╚šúČŻŘ╚ŇúČĆV╬¸Ëđ4├ű┬╔Äčď┌┤˙└Ý═ČĎ╗Î┌░Ş╝■Ľr(shʬ)ϲ╔Š¤ËĚ┴║ŽÎ¸ÎC▒╗▒▒║ú╩đż»ĚŻÄžÎ▀íúď┌4├űŮqÎo(hĘ┤)┬╔Äč▒╗ÎąÁ─Á┌17╠ýúČ╬ĎĆ─żW(wĘúng)Żj(luĘ░)╔¤┐┤ÁŻ┴╦í░Śţď┌đ┬┬╔ÄčĎĐŻŤ(jĘęng)▒╗┼˙▓ÂúČ┴Ý═Ô╚ř╬╗┬╔Äč▒╗╚í▒ú║˛?qĘ▒)Ćí▒Á─¤ű¤óí?br>
íííííşíş
ííííčo(wĘ▓)Ňô╩ăí░│╠đ˛í▒│╔×Úí░╩Í└m(xĘ┤)í▒úČ▀Ç╩ă│╔×Úí░▀^(guĘ░)ł÷(chĘúng)í▒úČÂ╝┼c╚╦éâîŽ(duĘČ)Ňř┴xÁ─Ă┌ďS┤Šď┌żÓŰxíúÍ┴Ë┌░Đí░│╠đ˛í▒«ö(dĘíng)θí░╣Ąż▀í▒╗˛Ň▀í░Ĺ═┴Pí▒úČätŞŘ╩ăîŽ(duĘČ)╣źĂŻŇř┴xÁ─ç└(yĘón)Íě┼Ąă˙íú═Ę▀^(guĘ░)▀@śËÁ─í░│╠đ˛í▒«a(chĘún)╔˙Á─ŻY(jiĘŽ)╣űúČčo(wĘ▓)ŇôŇř┤_┼cĚ˝úČčo(wĘ▓)Ňôđ╠Ă┌ÚL(zhĘúng)Â╠úČÂ╝ŰyĎďÎî╚╦Ě■ÜÔúČĎ▓╚ŢĎÎĎř░l(fĘí)╔šĽ■(huĘČ)ŕP(guĘín)Îóíú╔§Í┴úČ▀ÇËđ┐╔─▄Îî╚╦ŞđËX(juĘŽ)ÁŻŰ[Ű[Á─▓╗░▓íú
íííí▀@ŞŠďV╬ĎéâúČ│╠đ˛Ňř┴x▓╗âHîŽ(duĘČ)▒úҤîŹ(shʬ)ˇwŇř┴xĚă│úÍěϬúČ°ăĎîŽ(duĘČ)ď÷ĆŐ(qiĘóng)╚╦éâÁ─ĚĘ┬╔░▓╚źŞđĎ▓śO×ÚÍěϬíú╚š╣űŇ■Ş«¤ŰÎî╚╦éâ░▓żËśĚ(lĘĘ)śI(yĘĘ)úČż═▓╗âHϬ┐ěÍĂ̪δúČ┤_▒ú╣ź├˝¤ÝËđ╗¨▒żÁ─╔šĽ■(huĘČ)░▓╚źúČ▀Ç▒ěÝÜ┤_▒ú╚╦éâ¤ÝËđ╗¨▒żÁ─ĚĘ┬╔░▓╚źíú▀@ż═đŔϬ╩╣╚╦éâ¤Óđ┼úČ╦űéâ?cĘĘ)┌┼cĚĘ┬╔┤˛Ż╗Á└Ľr(shʬ)─▄ë˛Á├ÁŻ╣źĂŻÁ─îŽ(duĘČ)┤říú
ííííĎ╗éÇ(gĘĘ)▓╗─▄╠ß╣ę╣źŇřîĆ┼đÁ─ÁěĚŻúČ╩ă▓╗Ľ■(huĘČ)Îî╚╦ËđĚĘ┬╔░▓╚źŞđÁ─úČÎţŻKĎ▓╩ă▓╗Ľ■(huĘČ)Ëđí░╬ŘĎř┴Ží▒Á─(╔¤éÇ(gĘĘ)╩└╝o(jĘČ)90─ŕ┤˙│§úČ├└ç°(guĘ«)╣■Ě┤ˇîW(xuĘŽ)Ż╠╩┌╝s╔¬Ě˛íĄ─╬ż═╠ß│÷┴╦í░▄ŤîŹ(shʬ)┴Ží▒Á─Ş┼─ţíúí░▄ŤîŹ(shʬ)┴Ží▒│ú│ú▀Ç▒╗▒Ý╩÷×Úí░îž(dĘúo)¤˛┴Ží▒íóí░╬ŘĎř┴Ží▒║═í░đžĚ┬┴Ží▒)íú°îŽ(duĘČ)╚╦éâĚĘ┬╔░▓╚źŞđÁ─Îţ┤ˇ═■├{úČ▓╗âHüÝ(lĘói)ÎďË┌îŹ(shʬ)ˇw▓╗╣źúČŞŘüÝ(lĘói)ÎďË┌│╠đ˛▓╗╣źíú
ííííϲ?yĘĄn)ÚúČî?shʬ)ˇw╣źŇř═¨═¨╩ă│Ú¤ˇÂ°─ú║řÁ─úČ°│╠đ˛╣źŇřät═Ę│ú╩ăż▀ˇw°├¸┤_Á─íúîŽ(duĘČ)Ë┌Ď╗éÇ(gĘĘ)Ť](mĘŽi)Ëđůó╝ËĚĘ═ąîĆ┼đËÍ┼c░Ş╝■Á─╠Ä└ÝŻY(jiĘŽ)╣űŤ](mĘŽi)ËđÍ▒ŻË└ű║ŽŕP(guĘín)¤ÁÁ─╔šĽ■(huĘČ)╣ź▒ŐüÝ(lĘói)Ňf(shuĘş)úČ╦űď┌┼đöÓĎ╗éÇ(gĘĘ)░Ş╝■Á─îĆ└Ý╩ăĚ˝╣źŇřĽr(shʬ)úČ͸Ϭ╩ă┐┤▀@éÇ(gĘĘ)░ŞÎËÁ─îĆ└Ý▀^(guĘ░)│╠╩ăĚ˝╣źŇříú°ăĎúČ┼đöÓĎ╗éÇ(gĘĘ)╔šĽ■(huĘČ)╩ă║├╩ăë─úČ▓╗╩ă┐┤í░ë─╚╦í▒ËđŤ](mĘŽi)Ëđ▒╗Ě┼┐vúČ°╩ă┐┤í░║├╚╦í▒ËđŤ](mĘŽi)Ëđ▒╗ďę═¸úČ▓╗╩ă┐┤í░║├╚╦í▒Á─ÖÓ(quĘón)└űËđŤ](mĘŽi)ËđÁ├ÁŻ▒úҤúČ°╩ă┐┤─ăđę▒╗ÂĘ┴x×Úí░ë─╚╦í▒Á─ÖÓ(quĘón)└ű╩ăĚ˝Á├ÁŻ▒úҤíú
ííííďç¤ŰúČď┌Ď╗éÇ(gĘĘ)╔šĽ■(huĘČ)úČ╚š╣ű▀Bí░ë─╚╦í▒Á─ÖÓ(quĘón)└űÂ╝─▄Á├ÁŻ│╠đ˛▒úҤÁ─ďĺúČ─ă├┤úČí░║├╚╦í▒Á─ÖÓ(quĘón)└ű▀ÇĽ■(huĘČ)│╔×Úćľ(wĘĘn)ţ}ćß?!
ҬÎď: └ţ?yuĘĄn)^´wÍ° íÂ│╠đ˛║¤ĚĘđďĐđż┐:Ďďđ╠╩┬ďVďAĚĘ×ÚĚÂ└říĚ
┬Ľ├¸ú║ďôĽ°Ň¬Ë╔▒żŇżĺ▀├ŔńŤ╚ŰúČâH╣ęŻÚŻBłDĽ°╩╣Ë├úČňe(cuĘ░)Ň`ď┌╦¨Űy├ÔúČĎřË├Ľr(shʬ)Ňł(qĘźng)┼cﺼ°║╦îŽ(duĘČ)í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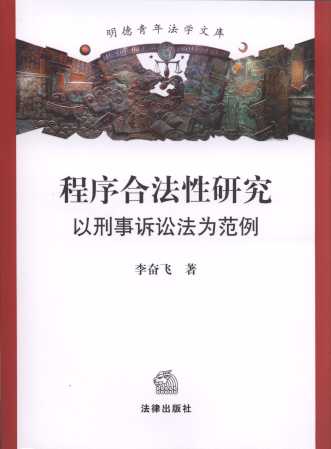 ŕP(guĘín)Ë┌í░│╠đ˛í▒Á─öÓ¤Ű(┤˙║ˇËŤ)íí
ŕP(guĘín)Ë┌í░│╠đ˛í▒Á─öÓ¤Ű(┤˙║ˇËŤ)í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