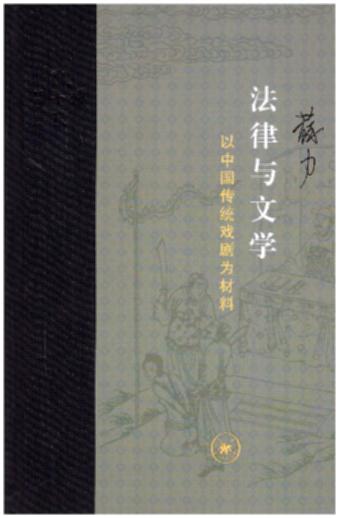
附錄1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
法的關系……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
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它們根源于物
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
一
我從近年中國的兩部頗為上座的、反映當代中國農村法治建設的電影談起。
第一部電影是《秋菊打官司》,講的是西北農村中的一個糾紛處置(而不是解決)。為一些并不很緊要的事,一位農民同村長吵起來了,罵村長“斷子絕孫”(村長的確只生了四個女兒)。這種話在中國的社會背景(尤其在農村)下是非常傷人的。憤怒的村長和這位農民打了起來,向村民的下身踢了幾腳。村民受了傷。村民的妻子——秋菊為此非常憤怒。她認為,村長可以踢她的丈夫,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她要討個“說法”,大致是要上級領導批評村長,村長認個錯。由于這種糾紛在中國農村并不少見,而且傷害也不重,因此鄉間的司法助理員沒有給予這位村長正式的處罰,而是試圖調解一下。調解不能令秋菊滿意,于是她先后到了縣城、省城計“說法”。經過種種努力,最后在一位律師的幫助下,上級派來了公安人員調查,發現該村民受到了輕傷害(但不是下身受到傷害),加害人應當受到治安處罰。村長被處以15天的行政拘留。但在告知秋菊這一決定、村長被帶
走之際,秋菊說,怎么把人給抓了,我只是要個說法。她站在村頭的公路籩,看著遠去的警車,滿臉的迷惑不解:為什么法律是這樣運作的? 第二個電影是《被告山杠爺》。簡單說來,山杠爺是一個非常偏遠的、據說治安秩序很好的山村(縣鄉的治安人員都從來沒有來過)的村黨支部書記。他個人品質很好,非常受人尊敬,但他的職責和品性也使他與村里的一些人不時發生沖突,有時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強迫村民。村里有個年輕媳婦虐待婆婆,甚至打傷了婆婆,受到了全村人的譴責。山杠爺看不過,在該媳婦屢次打罵婆婆的情況下,命令人把這個媳婦抓了起來,游了村。游村是一種非常嚴厲的民間懲罰方式。羞愧和憤恨之下,青年婦女跳河死了。事情捅到了上級司法機關,公安人員逮捕了山杠爺,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權。
這里的介紹當然是大大簡略了,電影本身包含了更多的關于當代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的信息。對于這兩部電影,不少中國法律人和評論家的解釋是,它們反映了中國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眾已開始越來越多地運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2]然而,這兩部影片(尤其是《秋菊打官司》提出的問題很多,底蘊很豐富,顯示出“形象大于思想”的特點,因此任何理性的解釋在對于形象的直覺感悟面前都往往顯得簡單、枯燥和拙劣。盡管如此,理智的、叫真的追問卻可以使那些不明確的、也許是一閃即逝的感觸得以明確和確定,使那些讓我們動情的東西以思辨的形式昭示于人間。
當然,本文不可能、也不準備對影片的內涵作全面分析。本文將集中討論:當我們看到一種據說是更為現代、更加關注公民權利保障的法治開始影響中國農村時,究竟給農民帶來了什么,這種“現代的”法治在他們那兒能否運行,其代價是什么?
二
就本文的實質性問題而言,這兩部電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是否存在一種無語境的、客觀普遍的權利,可以毫無疑問地據此建立一個普適的法律制度來保護這種權利。通常的觀點,以及這兩部電影所展現的法律實踐中隱含的觀點,都是一種普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存在這種普適的權利界定,特別是在一些西方學者通常稱之為基本性的權利上:安全、自由和財產權。盡管這種基本和非基本的權利分類在理論上早就受到質疑,但在實踐上仍然很有影響,包括在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當代中國的正式法律和法律運作都受到了這種意識形態的重大影響。
但是,就秋菊的案件來看,這種觀點有很大缺陷。例如,秋菊說,村長可以踢她丈夫,但不能踢她丈夫的下身,這種關于權利的界定明顯不同于
法學界的權利界定。又例如,盡管正式的法律沒有規定,但在中國農民和許多城市公民心目中,都會認為罵別人斷子絕孫(哪怕說的是事實)也是對他人的嚴重傷害,這種傷害甚至要比某些身體傷害更為嚴重,是對公民“權利”的一種侵犯。然而,我們的正式法律制度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是依據那種進口的觀點構建起來的,因此,身體的傷害是傷害,而語言、至少“斷子絕孫”這樣的語言不構成傷害。
當然如果僅僅是傷害分類不同,或這一分類僅僅停留在語言的層面,那也無所謂。重要的是語言具有構造現實、影響現實的力量,特別是法律的語言。伴隨這種定義和分類而來的是一個正式法律的運作邏輯及其帶來的社會效果。在《秋菊》的糾紛中,當司法機關沒有發現秋菊丈夫受到身體傷害時,正式法律就將這一糾紛推開;而一旦證實有較為嚴重的身體傷害時,伴隨的則是法律上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被認為是恰當的、合理的解決糾紛的方式,而沒有給予秋菊所要求的“說法”。甚至這個正式
的法律制度無法理解、也沒有試圖理解什么是秋菊要的“說法”。我說的是這個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這個制度中的運作者;其實這個制度中的絕大多數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知道秋菊的“說法”大致是什么;僅僅因為在這個法律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上沒有這個“說法”的制度空間,因此無法理解“說法”這一不合所謂的現代法治模式的請求。[5]換言之,只有符合這一法治模式的請求才構成訴訟請求,才能進入這一程序。在這里,制度的邏輯限制了一種人人知道的知識以及其他可能性。如果不是將法治理想化、甚至烏托邦化的話,應當說,在這里,實際就是法治——規則在統治,而不是人們以他的私人知識根據具體的情況作出裁決,即使這樣的裁決是合乎情理的。[6]
必須承認這種法律運作作為制度的合理性。我并不僅僅因為這一個案子的得失就主張回到那種由某個圣明智慧、公正廉潔的個人依據個人洞識恰當處理個案的人治模式;那樣的人治可能會產生完美的結果,但——即使裁決者個人品質無可指摘——也完全可能產生暴政。從長遠看來,從發展趨勢和社會條件來說,中國都必須建立制度化的法律,建立法治。但我們知道,任何制度性法律都不可能完滿地處理一切糾紛,都必然會有缺憾之處。從這個角度看,這一法律制度具有總體上的合理性。的確,對于許多受過正式法律教育的人(包括我自己)來說,可能都會認為,正式的法律制度更為正義,更具合理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正式的法律制度沒有改進之處。因為正義和合理性并不是大寫的。借用麥金太爾的一部書名,那就要問一問“誰家的正義?何種合理性?”。如果 按照那種普適的、客觀的權利觀和法律制度,權利和權利保護都將以一種外來的觀念來界定,而對于人們的“地方性知識”(再借用吉爾茲的一部書名)卻沒有給予多少重視。
必須指出,我并不反對吸取西方的觀念和法律制度,我主張對任何觀點都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然而我的確對那種大寫的普適真理持一種懷疑,因為這種大寫的真理有可能變得暴虐,讓其他語境化的定義、思想和做法都臣服于它。在近現代歷史上這種經驗教訓并不少見。[7]
就秋菊的情況來看,秋菊的要求更為合乎情理和可行,而且其社會后果也更好一些。因為在我看來,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根本目的都不應當是為了確立一種威權化的思想,而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調整社會關系,使人們比較協調,達到一種制度上的正義。從這個角度看,界定權利和建立權利保護機制的權力應當是分散化的,在可能的情況下應更多地考慮當事人的偏好,而不是依據一種令人懷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因此,至少從秋菊的困惑來看,我們應當說,中國當代正式法律的運作邏輯在某些方面與中國的社會背景脫節了。
持這一立場并不必然意味著我完全同意秋菊的權利界定。我可能不同意。但假如可以發現我的觀點更接近那個大寫的真理的話,也許可以把我的觀點強加他人,但問題是至少目前的研究表明不存在這種符合論意義上的真理,[8]那么,也許我們應當考慮的就是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哪一種定義和權利保護機制更有利于社會發展和社會和諧,均衡了相關各方的利益。
摘自:《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精)》,蘇力著,
內容簡介:試圖拓展當代中國法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法律與文學。我將主要以中國的一些傳統 戲劇為材料,分析法律的或與法律相關的一些理論問 題。
盡管運用的材料是文學的、歷史的并因此是地方性的,我的根本關切卻是當下的、現實的因此是一般性的。這種關切表現為,首先,我試圖從理論邏輯上 闡明——而不是傳統的“諷喻”或暗示或影射——這些問題對于今天中國法律與秩序之建構形成的相關性 ;其次,在這一努力中,我希望創造中國的法律與文學研究作為法學理論研究的一個分支的可能,以及更一般地——與我先前努力一致——創造在中國思考我 們的、同時具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問題的可能性。前者關注的是法律制度;而后者關注的是法律理論。
微店鏈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14958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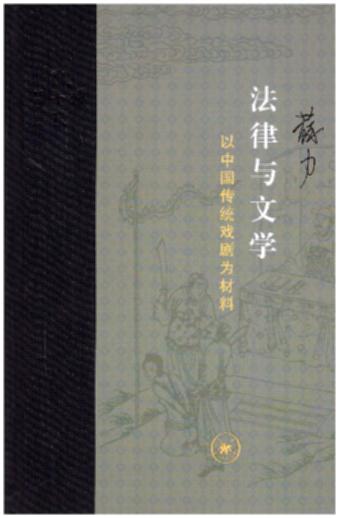 附錄1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
附錄1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