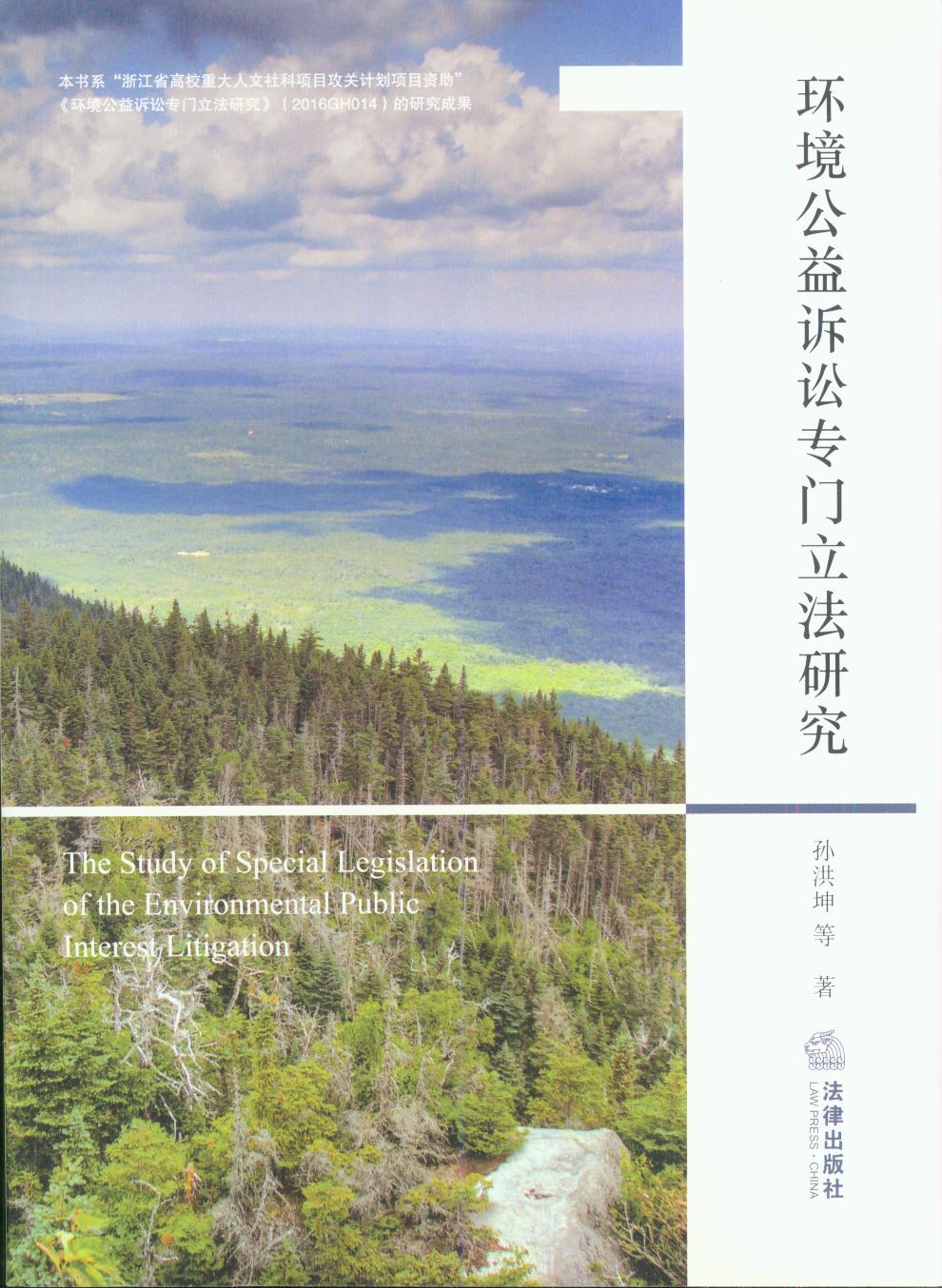
筆者雖主張法律應(yīng)賦予公民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但為防止反對(duì)者所擔(dān)心的濫訴、造成司法過重負(fù)擔(dān)等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在賦予其原告資格的同時(shí),確有必要設(shè)置一些規(guī)制條件。
(一)主體范圍應(yīng)受限制
提起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公民應(yīng)該是直接受到被訴行政行為影響的眾多人中的一分子,如果與被訴行政行為沒有任何直接利害關(guān)系,則不應(yīng)被賦予原告主體資格。這樣的限制目的有二:一是與原告主體資格之利害關(guān)系理論相銜接,二是防止濫訴情形的發(fā)生。
(二)不能獲得特別私利
公民在提起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時(shí),其訴訟請(qǐng)求范圍限于責(zé)令作出某行為、責(zé)令不作出某行為、恢復(fù)原狀等,而不包括行政賠償。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監(jiān)督公權(quán)力不亂政、不懶政,若訴訟請(qǐng)求獲得支持,則提起訴訟的公民雖與其他人一同受益,但其不能因此而獲得特別私利。
(三)實(shí)行復(fù)議前置程序
在提起訴訟前,應(yīng)窮盡行政救濟(jì)手段,實(shí)行復(fù)議前置程序。對(duì)復(fù)議結(jié)論不服的,才可提起訴訟。
(四)實(shí)行訴訟保證金制
要求公民在起訴時(shí),交納一筆承諾進(jìn)行正常訴訟的保證金,以防止其沒有正當(dāng)理由中途退出訴訟或無(wú)故不參加庭審等情形的發(fā)生。原告在進(jìn)行正常訴訟的情況下,最終無(wú)論其勝訴還是敗訴,保證金都要及時(shí)如數(shù)退還。
(五)引入“好事者”標(biāo)準(zhǔn)
“好事者”標(biāo)準(zhǔn)是澳大利亞為防止濫訴而制定的標(biāo)準(zhǔn),如果被告能證明原告起訴僅是為了騷擾,那么法院則可以原告缺乏主體資格為由駁回其起訴。在我國(guó)司法實(shí)踐中,確實(shí)有極少數(shù)人因與行政機(jī)關(guān)矛盾重重而不斷提起行政訴訟,故而澳大利亞“好事者”標(biāo)準(zhǔn)值得借鑒。
我國(guó)環(huán)境資源問題形勢(shì)日甚一日,已深深影響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進(jìn)程。客觀公允地說(shuō),相關(guān)環(huán)境資源行政部門的失位與錯(cuò)位是重要因素。化解環(huán)境危機(jī)的根本良方在監(jiān)管制度,主要依靠政府加強(qiáng)對(duì)環(huán)境資源污損者的監(jiān)管,而亂政、懶政是政府的兩大自身難以擺脫的弊病,故而需要設(shè)置監(jiān)督政府減少其弊病的制衡力量。很顯然,現(xiàn)階段僅賦予檢察機(jī)關(guān)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廣大公民是環(huán)境問題直接的利害關(guān)系人,監(jiān)督相關(guān)部門正確行使公權(quán)力是他們中的一些人的本能需求和強(qiáng)烈要求。因此,法律沒必要也無(wú)法對(duì)此視而不見。
摘自:《環(huán)境公益訴訟專門立法研究》P232-234頁(yè),法律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內(nèi)容簡(jiǎn)介:《環(huán)境公益訴訟專門立法研究》從立法條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角度論述了我國(guó)環(huán)境公益訴訟專門立法的意義和具體構(gòu)建,通過分析解構(gòu)現(xiàn)有的環(huán)境行政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制度、檢察機(jī)關(guān)提起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問題、環(huán)境行政執(zhí)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程序,探討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專門立法模式,包括原告資格、證據(jù)保全、程序銜接等。這一研究對(duì)于走向通過環(huán)境程序法治促進(jìn)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和環(huán)境治理法治化道路具有劃時(shí)代的意義。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e3c1debUn0WmE&id=568968560994
微店鏈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531668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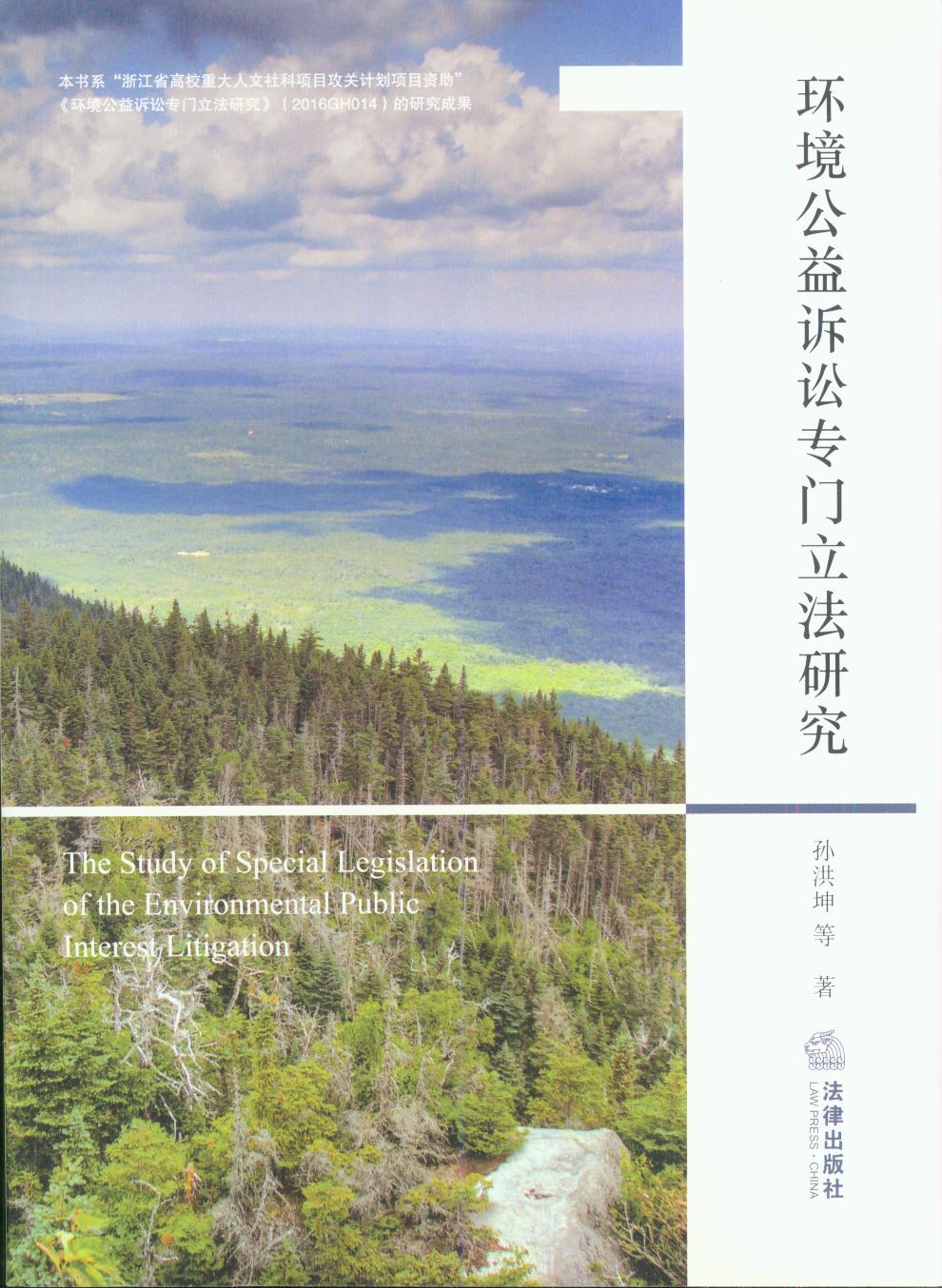 筆者雖主張法律應(yīng)賦予公民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但為防止反對(duì)者所擔(dān)心的濫訴、造成司法過重負(fù)擔(dān)等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在賦予其原告資格的同時(shí),確有必要設(shè)置一些規(guī)制條件。
筆者雖主張法律應(yīng)賦予公民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但為防止反對(duì)者所擔(dān)心的濫訴、造成司法過重負(fù)擔(dān)等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在賦予其原告資格的同時(shí),確有必要設(shè)置一些規(guī)制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