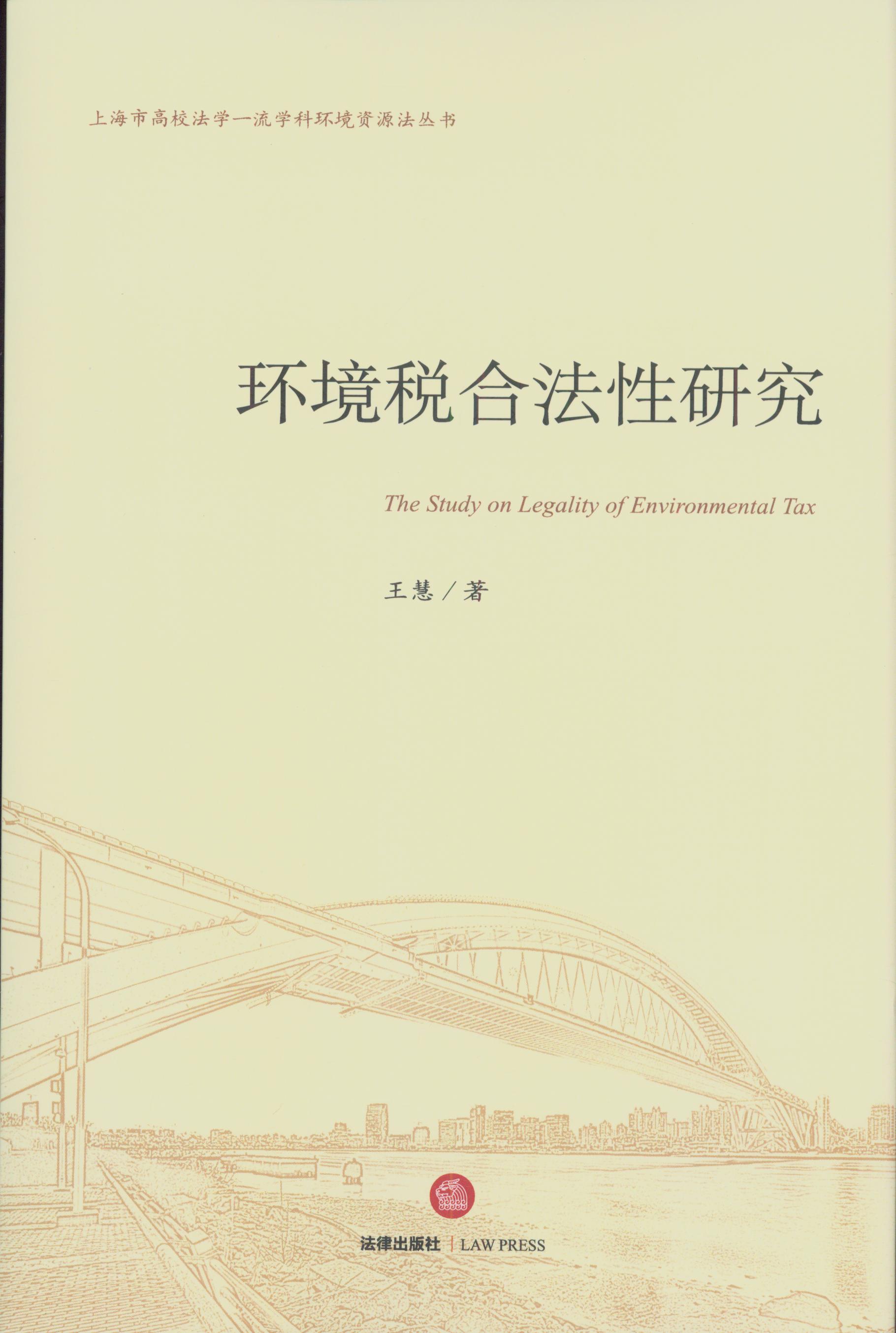
根據國民待遇條款,有些國內規則和稅收表面上似乎是非歧視性的,但是,實際上由于市場或其他各種情況,使這些規則或稅收產生了歧視進口產品的效果,從而導致“隱形歧視”的存在。“由于在各種國內機構中,涉及GATT規則的復雜程度逐漸增大,因此涉及“隱形歧視”案件也在增加,美國征收酒精類飲料稅所導致的國際貿易糾紛就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平等對待條款”不僅規范國民貿易中具有“外在歧視”效果的國際貿易措施,而且規范國際貿易中具有“隱形歧視”的國際貿易措施。根據“平等對待條款”,基于環境保護目的的環境稅措施通常受到多邊貿易體制的諸多限制。
從環境保護和國際貿易自由化的角度來看,環境稅制度通常具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環境稅制度具有“外在歧視”特性,即針對相同的產品實施差別的稅收制度,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環境稅制度由于具有改變人們行為的功效所以具有積極意義;二是從貿易自由化的角度來看,環境稅制度具有“自我強化的歧視效應”( self-reinforcingdiscrimination effects)。如果我們假定環境稅可以誘導產品制造者改變產品的生產方法使其對環境破壞效果減弱,那么我們可以認為那些與產品銷售市場聯系較緊密的生產者將會改變其產品生產,而那些與產品銷售市場聯系不夠緊密的生產者將可能不會承擔改變產品生產程度的成本。由于國內市場與國內產品生產者的市場占有份額關系比國外產品生產者的市場占有份額較大,所以國內產品生產者比國外產品生產者更愿意改變產品的生產方法。結果會導致環境稅逐漸具有歧視效果,即便環境稅制定之初具有歧視效果。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執行環境稅的國家會確保進口產品的稅收和國內產品的稅收一樣多。此外,在沒有該類產品進口的情況下,該稅就成為國外生產者進入國內市場的障礙。迄今有關環境稅“隱形歧視”的案件是“美國汽車稅案”,該案主要涉及“油老虎稅”的“隱形歧視”,美國的“油老虎稅”起初針對所有低于一定燃油效率的汽車,而且該稅的稅率隨著燃油效率的降低而增加。當該稅在1978年引進的時候其征收對象包括了大量的國內汽車,但是到1992年的時候該稅主主要針對來自歐盟的汽車進行征收,顯然這是因為國內汽車生產者已改變了產品的生產種類,而歐盟的汽車生產商并沒有改變產品的生產種類。
除了美國“油老虎稅”這樣逐漸產生歧視效果的環境稅之外,環境稅制度還可能導致其他種類的貿易歧視效果。有些環境稅制度從一開始便具有貿易歧視的效果,比如旨在鼓勵生產者回收產品廢棄物的產品押金返還制度( deposit-refund system),該制度給國外生產者所施加的成本大于給國內生產者所施加的成本,因為對于國外生產者而言要想收回自己生產產品的廢棄物必須投入更多的資金,但是對于國內生產者而言,這種規定所導致的成本不會大于國外生產者承擔的成本,這無形之中對國內生產者提供了保護。此外,當小規模生產者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小于大規模生產者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時,環境稅制度有時對小規模的生產者實行稅收優惠政策,這樣的制度一般有利于國內生產者,因為大規模生產者往往將產品銷售國外,而小規模生產者往往將產品銷售國內。有些環境稅制度對那些采用特定原材料的產品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當特定原材料無法以全球統一的價格獲取時,則會對有些國家的產品生產構成了貿易歧視,而對有些國家的產品生產形成了貿易保護。
從“隱形歧視”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來看,“隱形歧視”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針對產品的稅收區別主要建立在與產品生產國密切相關的一些特征上,比如有些產品是由那些來自特定國家的原材料所生產的。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國家的產品就會受到國內稅的歧視,從國民待遇的一般規定來看,這違背了GATT第3條。但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有利于環保,比如進口國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本國的環境免遭損害或者保護資源免遭過渡開采或枯竭。所以這時需要考慮GATT第20條,即政策的目的合法性成為判斷國內稅收是否違反GATT第3條的關鍵。但是,要想證明政策的目的合法具有很大的困難。另外一種是進口國間接地針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產品實行稅收區別,比如本國相關產品的生產由于環境稅制度的實施而早日改變,那么該環境稅制度可能對來自國外的相關產品構成事實上的貿易歧視。
雖然從貿易自由主義立場來看,“隱形歧視”顯然違背“同等對待條款”。但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隱形歧視”是否應該認定為違反“同等對待條款”則較為復雜,即針對進口產品的稅收不利待遇如何與針對國內產品的優惠稅收待遇進行比較。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進口產品的稅收稅負應該與國內一般產品相比,而不是與享受最優稅收的產品進行比較,否則會打擊進行環境保護的積極性。此時,雖然區別對待國內產品和進口產品的國內稅收并不當然導致國內稅收違反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但是在判斷國內稅收是否違反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時需要考慮歧視效果的地理分布(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iscriminatoryeffects)。一般而言,只要國內產品大體上比進口產品享受更優的稅收待遇,那么便可以認定該國內稅違反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有時只要稅收區別的歧視效應較為明顯,而且該國是相關產品的主要出口國,或者稅收區別主要與某一國家或某些國家集團的產品特征具有密切的關系,那么只要能夠證明某一國家的產品享受了較低的稅收待遇便可以認定該國的稅收措施違反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
此外,歧視效果的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時間點的選擇對于確定稅收措施是否違反GATT第3條第2款第1句同等重要。通常,有三種方法可以確定時間點:一是國內稅措施采納之時:二是相關爭議提交WTO之時;三是國內稅措施采納之時到相關爭議提交WTO的這段時間。采納爭議措施的國家傾向于選擇國內稅采納之時作為確定時間的方法,進口國可能認為讓其承擔由于隨后的事件發展而導致的國內稅對有些產品有利而對有些產品不利的責任不太公平。對于產業進口國而言,它們更喜歡選擇將相關爭議提交WTO之時作為確定時間的標準,因為這時它們遭受了產品競爭的影響。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選擇國內稅措施引入之時作為時間點較為理想,因為這時國內稅收措施反映了該稅收措施的目的。當然,鑒于環境稅的目的已實現,有人會認為既然目的已實現,那么就應該選擇爭議提交WTO之時作為確定時間的標準。但是,如果環境稅的廢止可能會導致意欲改變的產品和產品市場方法重新恢復原來狀況的話,那么就應該選擇國內稅引入之時作為確定時間的標準。所以,只有當環境稅的目的不再服務于初始目標時,才有必要選擇爭議提交WTO之時作為確定時間的標準。與此相關的一個案件是“美國汽車稅案”,但是該案既沒有裁決歧視效應的地域分配應該以國內稅收措施的引入之時作為基礎,也沒有明確說明爭議提交WTO之前的所有事項都無須考慮。可見,在裁決相關貿易措施是否違反“同等對待條款”時環境保護議題的地位尚不明確,這無疑會影響環境稅制度的合法性地位。
可見,如同“平等對待條款”中“外在歧視”的審查一樣,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平等對待條款”中“隱形歧視”的審查更多地出于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目的。因此,不管是“外在歧視”的審查還是“隱形歧視”的審查,都對一國的政治自由構成了限制,這限制了環境保護作為“平等對待條款”免除對象的可能性,進而使得環境稅制度難以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獲得合法性地位。
總之,“相同產品條款”(product-similarity clause)和“平等對待條款”(equality of treatment)是GATT非歧視原則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并相互影響。當有關平等對待的義務較為嚴格時,人們常對產品相同條款作狹義解釋,當有關平等對待的義務不嚴格時,人們常對產品相同條款作廣義解釋。同時,如果有關產品相同條款的解釋較為狹義時,人們往往對平等對待義務作嚴格解釋,如果有關產品相同條款的解釋較為廣義時,人們往往對平等對待的義務作并非嚴格的解釋。從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對“相同產品條款”“平等對待條款”的解釋中我們不難發現,環境保護逐漸成為多邊貿易體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環境要素現已成為“相同產品條款”的主要判斷標準。在多邊貿易體制將環境保護作為判斷國民待遇義務主要標準的背景下,環境稅制度無疑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合法性地位得到加強。雖然根據“平等對待條款”環境保護受到種種限制,因為環境保護尚未成為“平等對待條款”的主要例外理由,但是由于“平等對待條款”以“相同產品條款”為前提,所以環境稅制在多邊貿易規制中的合法性地位并未受到實質性挑戰,相反這種合法性地位正在逐漸得到強化。
摘自《環境稅合法性研究》P124-128頁,法律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內容簡介: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環境稅制度被人們寄托了改善環境品質的厚望,從財政改革的角度來看,環境稅制度被人們賦予了重構理性稅制的重任。雖然環境稅制度理論上具有改善環境品質和重構理性稅制的功能,但是奇怪的是環境稅制度的社會實踐背離了環境稅的理論預期。《環境稅合法性研究》在界定環境稅內涵的基礎上,分析我國現行環境稅費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提出解決方案和改革建議,推動我國環境稅制的完善。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1891debERUvUA&id=571721254518
微店鏈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558318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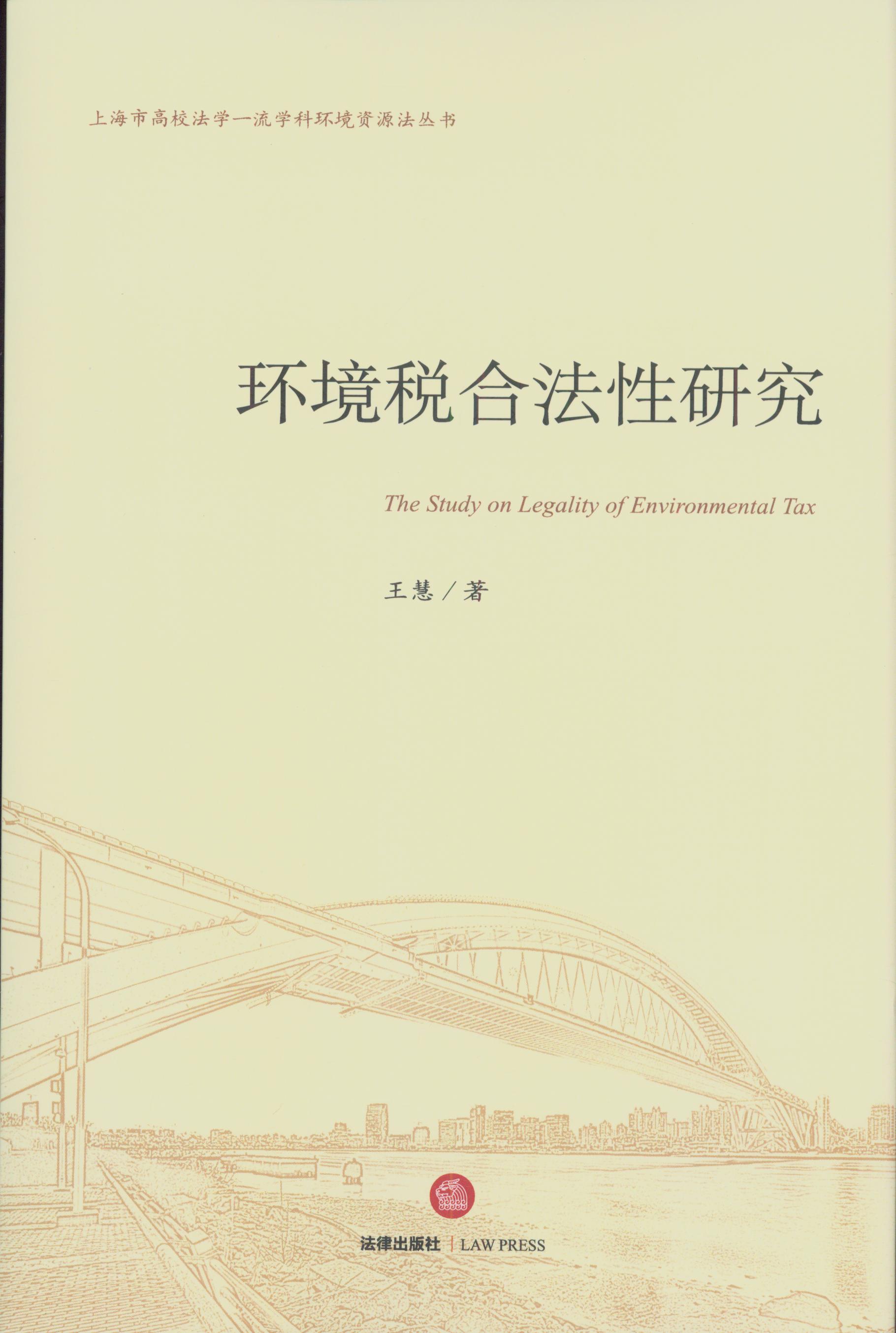 根據國民待遇條款,有些國內規則和稅收表面上似乎是非歧視性的,但是,實際上由于市場或其他各種情況,使這些規則或稅收產生了歧視進口產品的效果,從而導致“隱形歧視”的存在。“由于在各種國內機構中,涉及GATT規則的復雜程度逐漸增大,因此涉及“隱形歧視”案件也在增加,美國征收酒精類飲料稅所導致的國際貿易糾紛就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平等對待條款”不僅規范國民貿易中具有“外在歧視”效果的國際貿易措施,而且規范國際貿易中具有“隱形歧視”的國際貿易措施。根據“平等對待條款”,基于環境保護目的的環境稅措施通常受到多邊貿易體制的諸多限制。
根據國民待遇條款,有些國內規則和稅收表面上似乎是非歧視性的,但是,實際上由于市場或其他各種情況,使這些規則或稅收產生了歧視進口產品的效果,從而導致“隱形歧視”的存在。“由于在各種國內機構中,涉及GATT規則的復雜程度逐漸增大,因此涉及“隱形歧視”案件也在增加,美國征收酒精類飲料稅所導致的國際貿易糾紛就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平等對待條款”不僅規范國民貿易中具有“外在歧視”效果的國際貿易措施,而且規范國際貿易中具有“隱形歧視”的國際貿易措施。根據“平等對待條款”,基于環境保護目的的環境稅措施通常受到多邊貿易體制的諸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