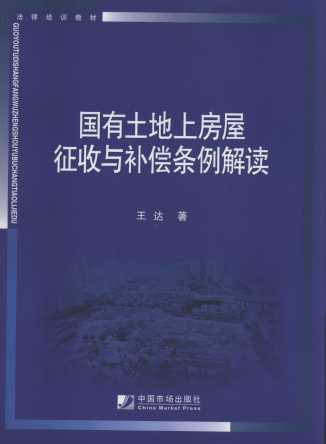
公共利益的域外比較
1.日本
日本雖立有《政府征收法》,但日本政府很少動用政府征收權,充分體現政府對私人財產的尊重和保護。例如,日本“最牛的釘子戶”因不肯搬遷,致使東京成田國際機場1號跑道拖延十多年才竣工,2號跑道無法修到規定長度致使飛機起降屢發險情,3號跑道至今還停留在圖紙上不能動工。2006年11月24日,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主持內閣經濟財政會議時提出,希望成田機場可以24小時起降飛機,然而也未能如愿。成田機場是日本最重要的國際機場,1966年,日本政府在新東京國際機場的幾處選址均遭到強烈反對后;便作出決定,遭到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許多業主發起了“一坪抵制運動”,將自家的土地以一坪(3.3平方米)為單位出手,以大量增加土地所有者,提高政府談判的難度。1971年,日本政府依據《土地征收法》采取強制措施,才征收取得機場1號跑道及配套設施所需要的土地。一些“釘子戶”在自己的土地上搭建了很高的鐵塔,妨礙飛機起降,與警察發生過嚴重對立甚至流血沖突,最后政府承諾不再強行動用《土地征收法》,機場與一些“釘子戶”訂立合同,明確約定夜間禁止飛機起降,以免影響他們的休息。直到1978年3月30日,1號跑道建成5年后才啟用。1999年為了承辦2002年韓日世界杯,當局啟動了2號跑道的修建工程,只好避開“釘子戶”,改道向北,原定2500米的跑道只修建2018米,一些大型客機無法起降。2005年7月15日,日本有關方面決定放棄向南延長跑道的談判,決定將跑道向北延伸。規劃中的3號跑道至今沒能動工。①
征收的項目能否成立,關鍵在于該項目是否具有公益性。②日本的《土地征收法》第三條采用列舉主義的方式,列出了可以進行征收或者征用的土地房屋的項目。只有符合該列舉出來的事項,才可以進行土地房屋征收征用。反之,即使被認為具有高度公共性的項目,只要未被列入《土地征收法》第三條的范圍,也無法采取征收的方式取得土地與房屋。
即使屬于《土地征收法》第三條所列出的項目,也并非理所當然馬上就可以進行征收。由于征收是將項目的公益性優先于財產所有權保護的制度設計,因此,必須要將征收土地和房屋的必要性付諸公共判斷,即首先需要進行項目認定。通過項目認定程序,需要判斷確定相關土地房屋、項目計劃以及為此該項目只能征收或者使用相關土地房屋的公益性。
2.意大利
舊城改造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進行,當政府與居民對公共利益理解產生矛盾時,所采取的解決方法,一是強化社區內部制衡的作用,將被拆遷人的利益補償通過社區來實現,避免被拆遷人直截了當與政府發生關系,也避免政府在舊城改造中孤軍混戰的局面;二是通過地區議會召開聽證會,讓被拆遷人參加聽證,使之面對面地闡述正反意見;三是事先將被拆遷人的利益示在媒體上,通過透明的操作程序,取得被拆遷人的理解與支持,化解可能產生的矛盾。
3.美國
在美國建國初期,私有財產排除政府干預、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深入人心。①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基于公共使用征收的立法原意得到普遍尊重。工業革命的興起逐漸沖擊私有財產保護的絕對性。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鼓勵資源開發,政府的征收活動在增加,這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私人財產成為公共利益的犧牲品。
1873年密歇根州米爾搭姆(Milldam)法令規定,通常情形為私人公司建造水力公司征收土地成為禁止,僅在“極大必需”的時候,才準許私人公司征收土地的權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其他很多州的最高法院在適用征收原則問題上持謹慎態度,即對公共使用采取狹義理解。1896年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訴內布拉斯加州案件中,美國聯邦法院認為,該州法案要求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準許農民們在其財產上建造安裝機器設備。雖然這些農民獲得利益,但社會大眾不能實際享受到該利益,法院因此認為該項計劃實質上是為了私人的利益剝奪私人財產,屬于違憲行為。
在該案發生20年之后,最高法院在林杰公司訴洛杉磯縣政府案中,認為并非只有在整個地區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數眾多的區域直接享受到其利益或參與其中,才能構成公共使用,在決定征收財產是否為公共使用所必需時,不僅僅應該看到當前公眾的需要,也要考慮在將來可以預期的需要。②1981年,美國底特律市政府征收了465英畝的土地,并廉價轉讓給通用汽車公司建造汽車制造廠。市政府認為,如果城市不能給通用公司提供新廠址,工廠將搬遷他處,將會喪失6 000個就業崗位,存在減少稅收等不利因素。最高法院維持了征收行為。③在1984年的“米德基夫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明確闡述了征收的“公用”的含義:只要征收權的行使和可見的公共目的理性相關,法院就必須判決征收符合公用目的。此乃“米德基夫標準”(Midkifftest)。①
4.德國
在經歷了近代公益征收、古典征收、魏瑪時代的“擴張性征收”以及基本法時代的公益征收之后,德國的公共征收制度趨于完善。《魏瑪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只因公共福利,根據法律規定方可財產征收,除聯邦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征收必須給予適當補償。”此乃世界上最早將征收的程序規定于憲法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在繼承魏瑪憲法相關規定的前提下,又發展了公共征收制度,將“公共使用”擴張為“公共利益”、“公共福祉”,并在憲法中得以體現,將公共利益視為最高層次,一般的行政權是實現國家任務的公權力行為,也是公共利益范疇。而政府征收是剝奪財產所有權的行為,所以政府征收不僅是為了一般的公共利益,而是重大公共利益。1950年德國巴登邦高等法院判決決定,并非所有公共利益都成為政府征收的理由,盡管為了實現國家及其他公共任務,國家斟酌這些任務而采取的措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但是,不一定能滿足公共利益之要件。②對重大公共利益的認定,要遵循“量最廣、質最優”的判斷標準。“量最廣、質最優”在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的內容是存在差異的。此,德國拉倫茲教授提出了以人民生存權及人類尊嚴為“公共利益”的最高價值。應當說形式法治的執法者和法官無法對“公共利益”作出客觀的、合乎理性的判斷,實質法治方能施展智慧法治之力量。
5.加拿大
加拿大地域遼闊,所有的土地在名義上都屬于女皇所有,這種所有實際上是虛化的,其處置權即使用權大部分歸私人所有,聯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也擁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征用土地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強制向私人收回土地的行為。征地的目的必須為公共利益服務,征地的范圍被限制在為公眾服務的交通、能源、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建設、文物保護、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公共利益的概念是狹義的,土地征用的范圍和條件很嚴格。一旦土地征用是為公眾服務,法定的征地機構就可以行使土地征用權。④
6.韓國
韓國有關部門征用土地除了依據《土地征收法》與《公共用地征得及損失補償特例法》外,還依據項目審批程序特例法、裁決申請期限的特別規定、管轄的特例、補償費的債券的特例,緊急用地特例法等都屬特別法,其法律效力優于一般法。因此,在韓國對于所謂特別法規定的項目都按《土地征收法》程序審批。《土地征收法》第三條列舉了可以進行土地征收或使用的項目,其中第八款規定“依法可以征用或使用土地的其他項目”,它概括規定了其他法律認可的公共事業。
韓國規定公用土地的征用必須有非常嚴格的目的性和強制性,即征用公共用地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所有者在項目發起人不放棄征用該土地的情況下,必須提供。根據韓國1991年修訂的《土地征收法》的規定,項目發起人為了公益事業要征用或使用土地時,必須依據總統令,接受建設交通部部長對項目的審查并獲得批準。根據《土地征收法》第二十五條,該項目在獲準公告之后,項目發起人為了征得或取消該土地使用權,應按總統令,與土地所有者及關系人進行協商。如果協商不能達成一致時,項目發起人則應自該項目獲準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管轄的土地征收委員會提出征用申請裁決。如果協商達成一致,也要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報土地征收委員會審核。經審核認可,即被視同為與依據《土地征收法》裁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據此,項目發起人、土地所有者及關系人不得再就協議內容發生爭議。最后根據征用辦理程序的順序,分階段實施。
韓國的土地征收委員會分為中央與地方兩級。建設交通部設有中央土地征收委員會,管轄國家確定的項目以及韓國稱為道的行政機構、漢城及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城市提出的項目。如果是跨越兩個以上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城市的項目,依然歸中央土地征收委員會管轄。在各個城市內的征用項目則由地方土地征收委員會裁決。韓國在土地交易中,實施嚴格的許可審批制。此外,由總統令認可的政府投資機構及公共團體,為了公共公益事業的需要使用土地時,為了確保公益用地,可以指定應該征購的購買方,由其進行所謂的協商征購。②
總之,上述國家在征收中對公共利益的理解,突出了尊重私權、聽證、制衡政府、禁止為商業目的進行征收等理念,值得我國在完善征收制度、公共利益立法等方面借鑒。
摘自:王達著《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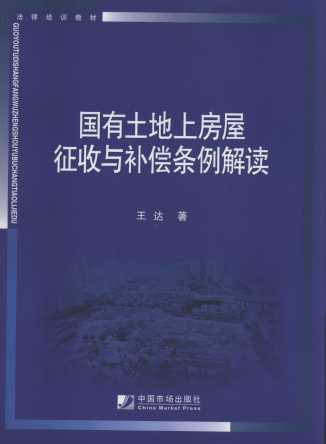 公共利益的域外比較
公共利益的域外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