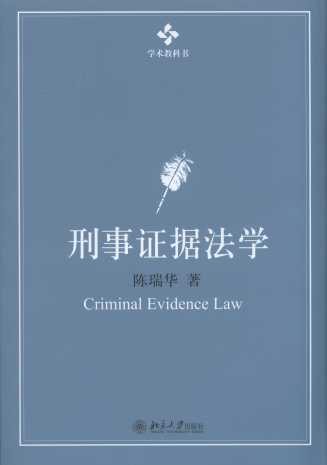
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的幾點反思
目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已經得到中國刑事訴訟法的確立和完善,并成為法律人普遍接受的證明標準。但是,這一證明標準也面臨著諸多方面的爭議和批評。
首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屬于司法證明的理想目標,而很難算得上一種可操作的“證明標準”。在哲學認識論中,“事實清楚”相當于“實事求是”或者“發現了事實真相”;“證據確實、充分”也就等于“證據在質與量上都滿足了證明要求”。歸結起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意思就是案件客觀事實已經被發現,達到了不枉不縱、客觀真實的程度。換言之,法官對待證事實的認定已經達到了百分之百的確定性,也就是完全恢復了曾經發生過的案件事實真相。但是,這一帶有哲學認識論意味的證明標準,以理想目標替代了可操作的證明標準,以至于實際否定了證明標準的價值。
其次,“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過于偏重對證明標準客觀層面的表述,而忽略了對法官內心確信程度的主觀層面。法律上的證明標準不僅要滿足客觀方面的確定性和真實程度的測量,而且還要著眼于法官對待證事實可信度的描述。而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表述中,我們看不到法官究竟對待證事實的真實性形成了多大程度的確信,是否存在合理的懷疑,而只發現了一種獨立于裁判者主觀認識之外的客觀目標。這種過于強調司法證明的客觀目標的立法表述方式,容易造成法官對“事實清楚”的含義作出任意解讀,以至于
享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權。事實上,在近年來得到披露的冤假錯案中,法院的有罪判決幾乎都曾作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表述。而在這些錯案得到糾正之后,同樣的法院根據同樣的證據往往又得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裁判結論。中國法院對定罪標準的解釋已經難以受到法律的有效約束了。
再次,證據法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所確立的法律規范,體現了一種“新法定證據主義”的立法理念,也就是對證據的證明力以及待證事實的真實程度確立了限制性的法律規則,而沒有交由法官根據經驗、理性和良心進行自由判斷。這與大陸法國家的自由心證原則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對定罪標準的法律規范,固然會發揮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積極作用,但卻以一種公式化的表述方式約束了法官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證據法不去規范和限制證據的合法性,卻要對法院定罪的標準確立一些近乎機械、刻板的法律規則,這可能不符合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容易造成法官的機械司法,使法官成為適用證據規則的機器和奴隸。
摘自: 陳瑞華 著《刑事證據法學/學術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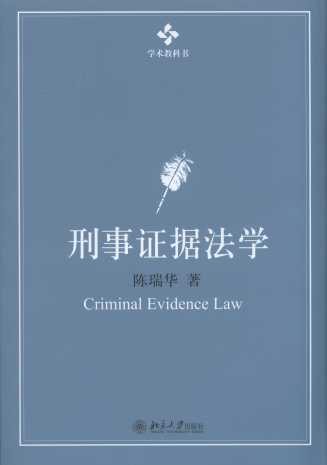 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的幾點反思
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的幾點反思